Meta 计划于 9 月的年度 Connect 大会上发布代号为 Hypernova 的新款智能眼镜。这是该公司首款面向消费者的智能眼镜,配备显示屏,...
2025-08-24 0
2025年5月4日,杭州市民在文三数字生活街区的AI黑科技市集上体验deepseek的人工智能大模型。(视觉中国|供图)
在AI时代,经过大数据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叠加与迭代,由站在个人之外的技术手段可以将个人在网上的所有往事毫无遗漏地记录下来而且不会被遗忘。
而被遗忘又恰恰是个人在主动或被动遭遇不堪事件后人格自我修复和自由发展的最关键条件。互联网、大数据技术以及人工智能所形成的不可被遗忘性,构成了捆绑现代普罗米修斯的永远也挣不断的铁链,往事被不断重提就犹如每天去啄食普罗米修斯肝脏的鹫鹰。
在我国,尽管司法实践多次遭遇原告的被遗忘权主张,但是司法裁判并没有依据当时有效的司法解释和后来施行的民法典中“其他人格权益”条款以及隐私的“私人生活安宁”条款,与个人信息保护法上的删除条款,解释和发展出本土化的被遗忘权。
这种做法无疑是谨慎且合法的,但并没能给予原告以个案正义,因为被遗忘权与社会公共利益(预防或打击犯罪、保护公众知情权等)存在较为激烈的冲突,没有更高的、更强的推动力,司法实践就无意在被遗忘权领域作出激进的回应。
2014年5月,欧盟法院所作出的“谷歌公司诉冈萨雷斯案”判决,点燃了公众对大数据时代的被遗忘权的关注,奠定了以删除权为特色的被遗忘权,而且直接影响到了其他国家。
俄罗斯在2015年7月即完成“被遗忘权法案”(Закон о праве на забвение)立法程序,建构了以删除权为特点且具有域外适用效力的实体法和程序法上的被遗忘权。2016年5月4日正式公布的GDPR第17条所规定了“删除权(被遗忘权)”。
被遗忘权的浪潮也波及我国的司法与理论。
2015年7月,在被称之为我国被遗忘权第一案的“任甲玉与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人格权纠纷案”中,当事人主张并提出以删除为基本诉求的被遗忘权问题,司法机关回应了对被遗忘权的裁判立场——“我国现行法律中并无对被遗忘权的法律规定,亦无被遗忘权的权利类型”,由此凸显了被遗忘权的本土化问题的现实意义。
2021年1月1日施行的民法典专章规定了“隐私权与个人信息保护”,特别是“私人生活安宁”被纳入“隐私权”的范畴,而2021年11月1日施行的个人信息保护法第47条专门规定了删除权。
但是,司法实践并没有因此承认被遗忘权。
被遗忘权存在与否的试金石是关于犯罪前科能否作为隐私权或个人信息被保护的问题。因为有关犯罪前科,也即犯罪记录,在令人难堪的往事中是最令人难堪的。与民法典同时施行的、经修订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2条统统被删除,而在原第12条中“犯罪记录”被明确地作为“个人信息和其他个人信息”,其在被“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公开”造成他人损害时,被侵权人可以请求其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
2024年7月18日《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部分,作为“健全公证执法司法体制机制”的内容,提出“建立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奠定了被遗忘权制度本土化建构的中国特色。2025年6月,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三审通过。为贯彻落实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三审稿对治安违法记录封存作出规定。
针对最难解决的“犯罪记录”问题,中国采取的是刑事基本法律先行的方法,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新增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但是,缺乏对司法机关和相关行政部门如何实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实体性和程序性问题的具体规定,导致在刑事诉讼法引入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后十年,效果依然令人难以满意。
根据两高两部《关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实施办法》的新闻稿披露:“实践中对封存的主体、封存的具体内容和程序以及查询的主体、内容、程序等把握不一,导致该制度在落实中出现封存管理失范,相关部门监管失序等问题。如一些企业违法提供、出售、使用未成年人犯罪记录,致使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泄露等”。
2022年5月两高两部共同发布了《关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实施办法》,意在保障未成年人在就学、就业、生活保障等方面受到同等待遇,“尽可能降低轻罪前科对未成年人回归社会的影响,促使其悔过自新、重回正轨”。
根据该办法,“应当封存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包括侦查、起诉、审判及刑事执行过程中形成的有关未成年人犯罪或者涉嫌犯罪的全部案卷材料与电子档案信息”,而且“不予刑事处罚、不追究刑事责任、不起诉、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记录,以及对涉罪未成年人进行社会调查、帮教考察、心理疏导、司法救助等工作的记录,按照本办法规定的内容和程序进行封存”。“对于电子信息系统中需要封存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数据,应当加设封存标记,未经法定查询程序,不得进行信息查询、共享及复用。封存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数据不得向外部平台提供或对接”。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该实施办法明确了其与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关系,即“对于需要封存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应当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不予公开”,并且明确规定了“涉案未成年人应当封存的信息被不当公开”“不当泄露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或者隐私、信息的”法律责任。在未成年人保护领域率先承认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在个人信息保护法上的特殊地位,将其纳入个人信息保护法的保护范围,属于禁止国家机关以外的单位和个人处理的且须严格保密的个人信息,除符合解除封存的条件或依法查询犯罪记录外,不得被泄露,也不得披露“该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以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身份的其他资料”。
民法典和个人信息保护法均对犯罪记录在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法上的地位保持沉默,而与此同时,司法解释也急剧转向,令犯罪前科的保护问题再次成为悬而未决的问题。
然而,民事立法的漠视退缩激起了更大的要求改进犯罪记录保护的动力。以完善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新增加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为契机,2022年出台《关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实施办法》,为建立一般的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积累了经验。
在实施办法施行两年后,2024年7月18日,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以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方式,提出了建立(而非探索)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要求。
2025年6月,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三审通过,从新增加的内容来看,有相当部分的新增或修订条款是有关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的,包括:有关他人私生活安宁的,如采取滋扰、纠缠、跟踪等方法,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以及以产生社会生活噪音的方式,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如非法获取个人信息,以及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出售或提供个人信息的,进行人身检查,提取或者采集肖像、指纹信息和血液、尿液等生物样本以及其用途限制及其违反的责任。
最大的亮点莫过于对违反治安管理的记录的封存制度,首先是作为原则的一般要求,即“违反治安管理的记录应当予以封存,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或者公开”,其次是作为例外的特别限制,即“有关国家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属于例外,但立法同时也规定了有权进行查询的单位的保密义务要求,“依法进行查询的单位,应当对被封存的违法记录的情况予以保密”。
随着我国刑事犯罪结构的重大变化,轻微犯罪比例日增,曾经的犯罪人的再社会化问题成为重大的社会问题,导致该问题成为党中央高度关注的重要问题。决定要求“建立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凸显了问题解决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修订只是拉开了一系列围绕建立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系列修法的序幕,这也是我国被遗忘权本土化的最关键步骤:形成严格的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最终实现通过记录封存和限制查询范围,帮助犯罪人去除“标签化”,顺利入学、就业、重新回归社会。
(作者系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建文
责编 钱昊平
相关文章

Meta 计划于 9 月的年度 Connect 大会上发布代号为 Hypernova 的新款智能眼镜。这是该公司首款面向消费者的智能眼镜,配备显示屏,...
2025-08-24 0

临近8月底,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也即将到来,近期,国际社会的目光也汇聚到了中国的身上。这也是中国首次以轮值主席国身份主办上合组织峰会,作为维护多边主义的重...
2025-08-24 0

你每天用的手机,芯片可能来自韩国;开的汽车,发动机零件或许是日本机床加工的。这两个亚洲国家,在全球科技赛道上各有一手“绝活”,却又彼此较劲了几十年。如...
2025-08-24 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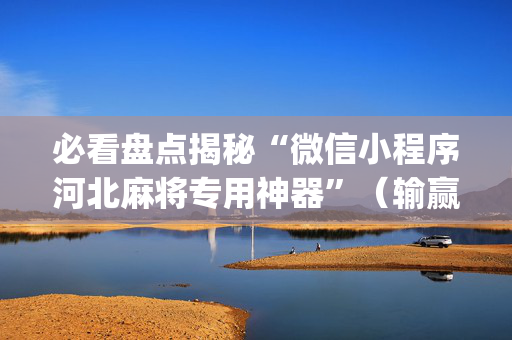
您好:这款游戏是可以开挂的,软件加微信【添加图中微信】确实是有挂的,很多玩家在这款游戏中打牌都会发现很多用户的牌特别好,总是好牌,而且好像能看到其他人...
2025-08-24 0

老杜还没离开拘留中心,他的家族便吹响反攻号角,马科斯遭遇强力阻击,亲姐姐带头背刺,莎拉是否已提前锁定菲律宾总统宝座?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还在荷兰海牙的...
2025-08-24 0

前言越南一边在南海占着中国29个岛礁,一边又厚着脸皮要中国分享高铁技术。这种"既要又要"的操作,连韩国人都看不下去了。8月14日,越南副总理陈红河会见...
2025-08-24 0

2025年8月,河北怀来地外天体着陆试验场,中国揽月月面着陆器圆满完成着陆起飞综合试验。这是中国第一次进行载人航天器地外天体着陆起飞试验,意味着我们离...
2025-08-24 0

您好:这款游戏是可以开挂的,软件加微信【添加图中微信】确实是有挂的,很多玩家在这款游戏中打牌都会发现很多用户的牌特别好,总是好牌,而且好像能看到其他人...
2025-08-24 0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