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需打开直接搜索微信:本司针对手游进行,选择我们的四大理由: ...
2025-08-26 0
在世界民航史上,很少有哪款飞机能像英国的霍克·西德利“三叉戟”(Hawker Siddeley Trident)那样,引发如此复杂而矛盾的情感。它的一生,是火焰与海水的交织,是荣耀与悲剧的共存。
一方面,它是无可争议的技术先锋。作为世界上第一款投入运营的三发喷气式客机,“三叉戟”拥有一系列划时代的创新 。其中最耀眼的,莫过于它那套革命性的“自动着陆”(Autoland)系统。这套系统使“三叉戟”成为全球首款能够在零能见度的“盲降”条件下获得认证并进行商业飞行的客机,彻底改变了全天候运行的游戏规则 。在伦敦希思罗机场常年弥漫的浓雾中,当其他飞机纷纷返航备降时,“三叉戟”却能像幽灵一样精准地降落在跑道上,这无疑是英国航空工业巅峰实力的展现。
然而,另一方面,它却是一款彻头彻尾的商业失败者。它的飞行员们给它起了一个不甚雅观的绰号——“抓地霸”(Ground Gripper),嘲讽它那孱弱的动力和因此导致过长的起飞滑跑距离 。在与宿命对手——美国波音727的全球竞争中,“三叉戟”一败涂地,其总产量仅为117架,而对手则卖出了惊人的1832架 。它的故事,充满了因商业短视、政府干预和市场误判而导致的无尽遗憾。它仿佛一件为特定客户量身定制、却最终发现完全不合全球市场身形的昂贵西装。
本文将深入剖析“三叉戟”客机的完整生命周期:从其宏大光明的诞生初衷,到改变游戏规则的先锋科技;从其在妥协中不断演变的复杂家族,到与波音727的宿命对决;从它在中国天空书写的独特篇章,到T型尾翼下隐藏的致命设计缺陷;最终,我们将探寻它留给后世的复杂遗产——这份遗产,甚至在今天的空中客车飞机上,依然能找到其历史的回响。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世界航空业正处于一个充满无限希望的黄金时代。作为英国国有的旗舰航空公司之一,英国欧洲航空公司(British European Airways, BEA)迫切需要一款新型的喷气式客机,以取代其在欧洲航线上日益老化的维克斯“子爵”式(Vickers Viscount)涡轮螺旋桨飞机 。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机队更新,更是大英帝国航空工业展示其技术实力、与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对手一较高下的绝佳机会。当时,英国航空制造业群星璀璨,各大公司都渴望赢得这份价值高达3000万英镑的巨额合同 。
在众多竞标者中,德·哈维兰公司(de Havilland)的方案脱颖而出。这家公司曾凭借世界上第一款喷气式客机“彗星”(Comet)开创了历史,尽管“彗星”的早期悲剧给公司蒙上了阴影,但其技术底蕴依然雄厚。他们提出的方案,名为DH.121,是一个极具雄心的设计 。
最初的DH.121方案,是一款旨在引领世界潮流的飞机。它被设计成世界上第一款三发喷气式客机,这种布局被认为是在巡航经济性和单发失效安全性之间的最佳平衡点 。为了追求极致的速度,其设计目标是巡航速度超过600英里/小时(约965公里/小时),这在当时是极为惊人的指标 。
在尺寸和性能上,DH.121是一款面向全球市场的中程干线客机。它计划搭载三台动力强劲的罗尔斯·罗伊斯“梅德韦”(Medway)涡扇发动机,最大起飞重量约63吨,在两舱布局下可搭载111名乘客,航程超过2000英里(约3330公里)。这是一个几乎完美的规格,完全符合当时全球航空市场对中程喷气式客机的主流需求。如果按照这个蓝图发展下去,“三叉戟”的命运或许将完全不同。
然而,就在德·哈维兰公司赢得合同,准备大展拳脚之际,启动用户BEA提出了一个足以改变项目命运的要求。由于当时航空市场出现了一次短暂的客流增长放缓,BEA的管理层做出了一个极其保守的判断:他们认为原版的DH.121对于其现有的欧洲航线来说“太大”了 。
作为唯一的启动客户,BEA手握项目的生杀大权。面对客户的坚持,急于获得订单以启动生产线的德·哈维兰公司别无选择,只能妥协 。他们被迫将原本宏伟的设计大幅“缩水”,以满足BEA的“定制”需求。这一决定,后来被证明是“三叉戟”项目的“原罪”,一个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其悲剧命运的战略性失误。
修改后的飞机,与最初的DH.121已判若两机。它换装了推力小得多的罗尔斯·罗伊斯“斯贝”(Spey)发动机,最大起飞重量被削减至约48吨,航程骤降至不足1000英里(约1500公里),载客量也减少到97至103人 。这款被阉割的飞机,在BEA举办的一次命名竞赛后,被正式命名为“三叉戟1型”(Trident 1)。
正当“三叉戟”项目在妥协中艰难推进时,英国航空工业自身也经历着剧烈的动荡。为了整合资源、对抗美国巨头,英国政府强力推行企业合并政策 。1960年,曾经辉煌的德·哈维兰公司被并入新成立的霍克·西德利集团(Hawker Siddeley),DH.121也因此被更名为HS.121“三叉戟” 。频繁的企业重组和管理层变动,无疑为这个本已充满变数的项目增添了更多的延迟和不确定性 。
从一款雄心勃勃、面向世界的“空中巴士”,沦为一款为单一客户的短视需求量身定做的“紧身西装”,这就是“三叉戟”悲剧的开端。BEA的误判,让霍克·西德利在“三叉戟”未来的整个生产周期中,都在拼命地试图通过拉长、增重、换发等方式,把它改回最初那个更强大、更具竞争力的样子。然而,他们始终都在扮演一个追赶者的角色,而这个致命的开局,早已为它在与波音727的竞争中败下阵来埋下了伏笔 。
尽管“三叉戟”的商业前景从诞生之初就蒙上了阴影,但这丝毫不能掩盖它在技术上的辉煌成就。作为一款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初的飞机,“三叉戟”身上凝聚了当时英国航空工业最顶尖的智慧,其中许多设计理念和技术应用,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1962年1月9日,“三叉戟”原型机成功完成首飞,成为世界上第一款飞上蓝天的三发喷气式客机,比其主要竞争对手波音727早了整整一年 。其独特的三发布局在当时是一种创新的选择。设计师们将三台发动机全部集中在机身尾部,两台通过挂架置于机身两侧,一台则埋藏在机尾内部 。
这种布局的最大优势在于,它能创造出一副空气动力学上极其“干净”的机翼。由于机翼上没有任何发动机吊舱的干扰,气流可以更平顺地流过翼面,从而优化了飞机在高速巡航时的气动效率,这也是“三叉戟”能达到极高巡航速度的关键原因之一 。
为了给位于机尾中央的2号发动机供气,设计师们采用了一个极具辨识度的S型进气道(S-duct)。气流从垂直尾翼根部进入,通过一个弯曲的S形管道被引导至发动机 。这种设计后来被证明非常成功,并被包括波音727、洛克希德L-1011“三星”在内的绝大多数后继三发客机所效仿,成为了三发客机的标志性特征 。相比之下,麦道DC-10采用的“直通式”尾部发动机布局,虽然结构简单,但在气动阻力上要大于S型进气道的设计 。
与尾置发动机相匹配的,是高高耸立的T型尾翼(T-tail)。这种设计将水平尾翼(平尾)置于垂直尾翼(垂尾)的顶端,使其远离下方发动机喷出的高温、高速、湍流的尾气,保证了尾翼的操纵效率 。然而,正如后文将要提到的,这个看似合理的设计,也隐藏着一个致命的空气动力学陷阱。
如果说三发布局是“三叉戟”在气动设计上的创新,那么其在航空电子领域的革命性创举,则彻底改变了民航飞行的历史。这项技术就是“自动着陆”系统。从项目伊始,“三叉戟”就被设计为一款具备全天候运行能力的飞机,其核心便是与史密斯工业公司(Smiths Industries)合作开发的SEP.5自动飞行控制系统 。
这套系统的核心理念是“冗余”与“表决”。它是一个“三工”(Triplex)系统,即拥有三个独立、并行的自动驾驶仪通道 。在自动进近和着陆过程中,这三个通道同时工作,并对各自的计算结果和操作指令进行实时比对。如果其中一个通道出现故障或数据异常,系统会通过“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2:1表决)将其自动“踢出”,由另外两个正常的通道继续完成操作 。这种三冗余设计,极大地保证了系统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是实现“盲降”的基石。
“自动着陆”系统的工作流程堪称精妙。在进近阶段,它通过接收机场仪表着陆系统(ILS)提供的航向道(Localizer)和下滑道(Glideslope)无线电信号,来精确控制飞机的水平和垂直轨迹 。当飞机下降至距离跑道约50英尺(约15米)的极低高度时,机上的雷达高度表会提供精确的高度数据,触发系统自动执行“拉平”(Flare)动作——即柔和地抬起机头,减小下降率,让主起落架轻柔地触地 。
这项技术的意义是颠覆性的。1965年,“三叉戟”在商业航班上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自动着陆 。随后,它不断刷新着民航运行的标准,先后在1968年获得二级(CAT II)、1972年获得三A级(CAT IIIA)、1975年获得三B级(CAT IIIB)运行认证 。这对于其主要客户BEA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福音。伦敦希思罗机场以其频繁的浓雾天气而闻名,每年冬季都有大量航班因此延误或取消,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而“三叉戟”的“自动着陆”能力,使得BEA的航班能够在其他航空公司望而却步的恶劣天气中正常起降,这不仅仅是技术上的领先,更是实实在在的运营优势。可以说,这项伟大的技术创新,正是为了解决其启动客户面临的特定地理和气候难题而诞生的。
为了容纳“自动着陆”系统所需的大量、笨重的电子设备(在那个晶体管和集成电路尚不发达的年代,这些设备体积巨大),设计师们在驾驶舱下方设置了一个宽敞的设备舱。为了给这个设备舱腾出空间,他们想出了一个绝无仅有的解决方案:将前起落架向左侧偏移了2英尺(约61厘米),并使其在收起时向侧方旋转折叠 。这个不对称的设计,成为了“三叉戟”外观上最独特的识别特征之一。
此外,“三叉戟”的驾驶舱内还配备了在当时极为先进的“移动地图显示器”。这是一个机电装置,通过多普勒导航系统计算飞机位置,然后驱动一个探针在一卷滚动的纸质地图上实时标示出飞机的位置,为飞行员提供了直观的导航参考 。
“三叉戟”的故事,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不断进行“亡羊补牢”式改进的故事。霍克·西德利公司在其整个生产周期中,都在努力弥补因最初的“缩水”决定而造成的性能和容量短板。这种被动的、反应式的开发思路,催生了一个成员众多但命运各异的“三叉戟”家族。
这是为BEA量身打造的最初生产型号。它搭载三台推力仅为10,050磅的“斯贝”505型发动机,动力储备严重不足,导致起飞性能不佳,“抓地霸”的绰号也由此而来 。其典型载客量为103人,航程有限,难以满足更广阔的市场需求 。在气动设计上,1C型采用了复杂的机翼前缘克鲁格襟翼和下垂前缘组合 。该型号共生产了24架,全部交付给了BEA 。
由于1C型完全是BEA的“特供版”,几乎没有出口吸引力,霍克·西德利公司很快推出了第一个改进型——1E型,这里的“E”代表出口(Export)。它保留了与1C型相同的机身长度,但在关键性能上进行了多项重要升级 。
首先,它换装了推力更大的“斯贝”511型发动机(11,400磅)。其次,机翼结构得到加强,翼展增加,并用更高效的前缘缝翼取代了1C型上的下垂前缘,显著改善了低速飞行性能 。此外,燃油容量也得到提升,使其航程和载客量(最多可达139人)都远超1C型 。尽管性能提升明显,但此时波音727已在市场上抢占先机,1E型的销售业绩依然惨淡,仅生产了15架 。
2E型是“三叉戟”家族中最成功、产量最高的型号,这里的“E”代表延程(Extended Range)。它是应BEA对更远航程的需求以及中国民航(CAAC)的巨额订单而开发的 。
2E型装备了当时“斯贝”系列中最强劲的512型发动机,单台推力提升至11,960磅 。其翼展进一步增加,并采用了经过气动优化的“库赫曼”(Kuchemann)翼尖,这种独特的弯曲翼尖设计有助于减小诱导阻力 。更大的燃油容量使其最大航程超过了2,400英里(约3860公里),终于达到了一个具有竞争力的水平 。2E型共生产了50架,其中大部分销往中国,成为了当时中国民航机队的绝对主力 。
进入60年代末,BEA再次发现需要更大载客量的飞机。他们曾考虑购买波音727,但该计划被英国政府否决,迫使他们再次转向霍克·西德利 。为了满足BEA的需求,同时又避免进行成本高昂的全新设计,霍克·西德利推出了“三叉戟”家族中最激进、也最奇特的改型——3B型。
3B型的机身被大幅拉长了超过16英尺(约5米),使其最大载客量一举提升至180人 。然而,问题也随之而来:大幅增加的重量使得沿用自2E型的“斯贝”512发动机在起飞时力不从心,尤其是在“高温高海拔”(hot and high)机场,飞机甚至可能无法离地 。
面对这个难题,霍克·西德利的工程师们展现了惊人的创造力。他们没有选择耗时耗力的全面换发方案,而是在机尾的S型进气道上方,也就是原本安装辅助动力单元(APU)的位置,加装了一台体积极小、重量极轻的罗尔斯·罗伊斯RB162微型涡喷发动机 。这台发动机的角色是“助推器”(Booster),它只在起飞阶段工作,提供额外的15%推力,而自身重量仅增加了5%。一旦飞机达到安全高度和速度,这台助推发动机就会被关闭 。这个“3+1”的四发设计,虽然看似怪异,却以极低的成本和重量代价,巧妙地解决了3B型的起飞性能问题。
此外,中国民航还购买了两架在3B型基础上增加了油箱容量的“超级三叉戟3B”(Super Trident 3B),这也是“三叉戟”家族的最后两个成员 。
下表清晰地展示了“三叉戟”家族各主要型号的演变过程:
型号 | 首飞日期 | 生产数量 | 发动机(主+助推) | 最大推力 | 机身长度 | 翼展 | 最大起飞重量 | 最大载客量 | 最大航程 |
Trident 1C | 1962年1月 | 24 | 3 x RR Spey 505 | 30,150 lbf | 34.98 m | 27.38 m | 52,163 kg | 103 | 2,250 km |
Trident 1E | 1964年11月 | 15 | 3 x RR Spey 511 | 34,200 lbf | 34.98 m | 28.96 m | 58,060 kg | 139 | 2,900 km |
Trident 2E | 1967年7月 | 50 | 3 x RR Spey 512 | 35,880 lbf | 34.98 m | 29.87 m | 65,090 kg | 149 | 3,910 km |
Trident 3B | 1969年12月 | 26 | 3 x RR Spey 512 + 1 x RR RB162 | 41,130 lbf | 39.98 m | 29.87 m | 68,040 kg | 180 | 2,400 km |
“三叉戟”的商业故事,始终笼罩在一个巨大而无法摆脱的阴影之下,这个阴影就是它的宿命对手——波音727。这两款飞机的对决,是世界民航史上最经典、也最令人扼腕的商业案例之一。
从外观上看,“三叉戟”与波音727惊人地相似。两者都采用了T型尾翼和三台尾置发动机的布局,以至于不熟悉的人很难将它们区分开来 。事实上,在项目早期,德·哈维兰和波音甚至还就DH.121和727项目进行过合作谈判,但最终未能达成一致 。
然而,历史最残酷的讽刺在于,波音727的尺寸、航程和载客量,几乎完美地复刻了“三叉戟”最初那个被BEA否决的、更大、更强的DH.121原始设计方案 。当霍克·西德利正在为满足单一客户的保守需求而打造一款“缩水版”飞机时,大洋彼岸的波音公司,却精准地把握住了全球市场的脉搏,制造出了世界真正需要的那款飞机。
随之而来的,是一场毫无悬念的商业“屠杀”。最终的生产数字冷酷地揭示了这场对决的结果:霍克·西德利在16年的生产周期里,总共制造了117架“三叉戟” 。而波音公司,则向全球的航空公司交付了多达1832架波音727 。超过15:1的悬殊比例,标志着“三叉戟”的完败。
波音727的成功并非偶然,它在多个关键领域都对“三叉戟”形成了压倒性优势:
下表直观地对比了“三叉戟”1C与波音727-100这两款宿命对手的初始数据,其间的差距,正是两者命运走向不同结局的根源。
技术规格 | 霍克·西德利 三叉戟 1C | 波音 727-100 |
机身长度 | 34.98 米 | 40.59 米 |
翼展 | 27.38 米 | 32.92 米 |
最大载客量 | 103 人 | 149 人 |
最大航程 | 约 2,700 公里 | 约 5,000 公里 |
最大速度 | 约 974 公里/小时 | 约 1,017 公里/小时 |
总产量 (所有型号) | 117 架 | 1,832 架 |
尽管“三叉戟”在全球市场上遭遇了滑铁卢,但它却在中国的天空找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归宿,并在此书写了一段充满传奇色彩的独特历史。对于中国民航和中国现代史而言,“三叉戟”不仅仅是一款飞机,更是一个时代的符号和一场政治风暴的见证者。
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中美关系解冻,中国开始打破多年的孤立,重新向西方世界打开大门。为了推动民航现代化,满足日益增长的国内及国际航线需求,中国民用航空总局(CAAC)急需引进一批先进的西方喷气式客机 。
在这样的背景下,购买英国的“三叉戟”客机,成为当时中国一项重大的政治和经济决策。这不仅是中国民航首次大批量引进西方喷气式客机,也是中英两国关系回暖的重要标志 。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这笔交易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商业范畴,它代表着一种开放的姿态和追赶世界先进技术水平的决心。
中国最终成为了“三叉戟”在全球最大的出口客户。这笔生意始于1970年,当时中国民航从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PIA)购买了4架二手的“三叉戟”1E型客机,用于初步的技术评估和人员培训 。
在获得了良好的使用体验后,中国民航在1971年与霍克·西德利公司签订了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合同,直接订购了6架全新的“三叉戟”2E型客机,合同总价值高达2000万英镑 。此后,订单不断追加,中国民航最终总共引进了33架全新的2E型和2架独一无二的“超级三叉戟”3B型 。1972年11月17日,首架崭新的“三叉戟”客机(编号B-2201)飞抵广州白云机场,正式开启了它在中国的服务生涯 。
在整个70年代和80年代,“三叉戟”机队成为了中国民航的绝对主力,承担着当时几乎所有重要的国内干线和周边国际航线的飞行任务 。它们的身影遍布北京、上海、广州等各大城市,是中国人民在那段时期最熟悉的喷气式客机。这批飞机一直服务到90年代初才陆续退役,其中一部分移交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作为高级官员的专机或特种任务飞机使用,据信最晚飞到1997年左右 。如今,在中国的一些城市和博物馆里,依然能看到退役的“三叉戟”客机作为静态展品,静静地诉说着那段历史 。
“三叉戟”的悲剧性,不仅体现在其商业上的失败,更铭刻在一场惨烈的空难之中。这场空难,暴露了其T型尾翼设计下一个致命的空气动力学缺陷——“深度失速”,并最终推动了全球航空安全法规的重大进步。
“深度失速”(Deep Stall),又称“超级失速”(Superstall),是一种极其危险的失速状态,主要影响T型尾翼布局的飞机 。
要理解深度失速,首先要明白普通失速。当飞机迎角(机翼弦线与来流空气方向的夹角)增大到临界值时,机翼上表面的气流会发生分离,导致升力急剧下降、阻力猛增,这就是失速。常规布局的飞机失速后,飞行员向前推杆,让机头下俯,减小迎角,飞机就能恢复速度和升力 。
然而,对于T型尾翼的飞机,情况则完全不同。由于其水平尾翼高高地置于垂尾顶端,当飞机以一个非常大的迎角失速时,从主机翼上表面分离出来的混乱、低能量的湍流尾迹,会正好向上向后流动,像一张大网一样将高置的水平尾翼完全“罩住”或“屏蔽”掉 。
这带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水平尾翼和其上的升降舵完全失去了作用,因为它们已经沉浸在没有稳定气流的“死水区”。此时,无论飞行员如何向前推杆,都无法让机头下俯。飞机就像被“锁死”在了大迎角失速状态,无法改出,最终会像一片落叶一样平拍着坠向地面 。
“三叉戟”的设计师们在早期的飞行测试中就已经发现了这种潜在的危险。为了防止飞机进入深度失速,他们为“三叉戟”安装了一套在当时非常先进的失速告警与保护系统,包括通过振动驾驶杆来警告飞行员的“抖杆器”(Stick Shaker),以及在飞行员无反应时能自动向前推杆、强制飞机低头的“推杆器”(Stick Pusher)。这套系统,本应是防止悲剧的最后一道防线。
1972年6月18日,一个阴雨的周日下午,这道防线被突破了。英国欧洲航空公司(BEA)的BE548次航班,由一架“三叉戟”1C型客机(注册号G-ARPI,呼号“Papa India”)执飞,从伦敦希思罗机场起飞,目的地是布鲁塞尔 。
起飞后不到三分钟,灾难降临。在飞机尚未达到足够的速度和高度时,机组过早地收回了机翼的前缘下垂装置(一种增升设备)。这一致命的失误,导致飞机速度迅速衰减,立即进入了失速状态 。失速告警系统被触发,抖杆器开始工作。然而,不知何故,飞行员却手动取消了自动保护系统。紧接着,飞机无可挽回地进入了深度失速,机头高高扬起,最终从空中坠落,砸在伦敦郊区斯坦斯镇(Staines)附近的一片田野里 。
机上118人(112名乘客和6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无一生还。这起事故在当时成为英国本土有史以来最惨重的空难 。
事故调查报告指出,空难的直接原因是飞行员失误:在不安全的速度下收回了增升装置,并在失速后采取了错误的处置,导致飞机进入了无法改出的深度失速 。
然而,调查也揭示了一系列深层次的诱因。首先,机长被发现在事发前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其健康状况可能影响了他在关键时刻的判断力。其次,副驾驶相对缺乏经验。更重要的是,当时BEA内部正因薪酬问题爆发激烈的劳资纠纷,飞行员队伍关系紧张,这种充满敌意的驾驶舱氛围,很可能分散了机组的注意力,导致了灾难性的疏忽 。
调查过程中一个最关键的障碍是,这架飞机没有安装驾驶舱语音记录器(CVR,即“黑匣子”之一)。调查人员只能依靠飞行数据记录器(FDR)和目击者证词来推断驾驶舱内发生的一切,而机组在最后时刻的对话、决策过程则成为了永远的谜 。
斯坦斯空难的惨痛教训,对全球民航安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调查报告最重要的建议,就是强制要求所有大型民航客机必须安装驾驶舱语音记录器。这项规定后来被全球采纳,成为了现代航空安全体系的基石,在无数后来的事故调查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这场悲剧,以118条生命的代价,揭示了航空安全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不仅关乎机器的可靠性,更深刻地交织着人的因素、组织管理和法规的完善。
当最后一架“三叉戟”在1985年从英国航空公司的机队中退役,并在90年代中期彻底告别中国的天空时,它为世界航空史留下了一份复杂而矛盾的遗产 。
它无疑是一个商业上的失败者。区区117架的总产量,在宿命对手波音727那近两千架的庞大数字面前,显得微不足道 。它的故事,成为了一个经典的商业教科书反面案例,深刻地揭示了一款技术产品如果脱离了广阔的市场需求,仅仅为了满足单一客户的狭隘、甚至是错误的规格要求,其命运将会何等坎坷。它警示后人,技术上的领先并不能必然转化为商业上的成功。
然而,它又是一个无可争议的技术先驱。它所开创的“自动着陆”技术,为现代民航客机的全天候运行奠定了基础,其标准至今仍在沿用 。它在航空电子领域的探索,是人类挑战飞行极限、追求更高安全性和效率的勇敢尝试。
更重要的是,“三叉戟”项目的遗产,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延续了下来。在开发“三叉戟”的过程中,德·哈维兰公司和后来的霍克·西德利公司,在设计和制造先进的高速后掠翼方面,积累了世界顶尖的宝贵经验和技术实力 。
这份技术财富没有被浪费。当霍克·西德利公司在70年代加入羽翼未丰的欧洲空中客车(Airbus)工业集团时,其卓越的机翼设计能力,成为了英国在这家泛欧企业中最核心的“嫁妆”。空客的创始人之一罗杰·贝泰耶(Roger Béteille)对“三叉戟”的机翼技术印象深刻,因此,为A300——空客的第一款飞机——以及后续所有空客机型设计和制造机翼的重任,便历史性地落在了英国人的肩上 。从哈特菲尔德到菲尔顿和布劳顿,这份源自“三叉戟”的机翼技术血脉,一直流淌至今,成为支撑起欧洲航空工业半壁江山的关键力量。
如今,“三叉戟”客机静静地停放在世界各地的航空博物馆里,它那流畅、优美甚至带有一丝科幻色彩的造型,依然在向人们诉说着那个属于它的、充满光荣与梦想,也充满遗憾与悲情的年代 。它的故事,是航空史上最引人深思的“假如”之一:假如BEA没有坚持己见,假如“三叉戟”能以其最初的宏伟蓝图问世,那么,20世纪后半叶的世界民航版图,或许将是另一番景象。这,就是“三叉戟”的悲歌,一曲献给技术理想主义的、壮丽而忧伤的挽歌。
相关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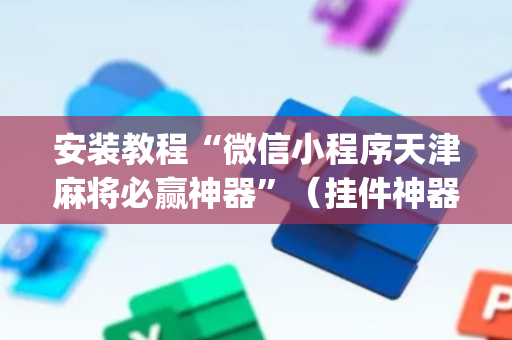
您好:这款游戏可以开挂,确实是有挂的,很多玩家在这款游戏中打牌都会发现很多用户的牌特别好,总是好牌,而且好像能看到-人的牌一样。所以很多小伙伴就怀疑这...
2025-08-26 0

近日,中国工程院公布了2025年院士增选有效候选人名单,包头市的中国北方重工业集团正高级工程师雷丙旺、核工业二零八大队正高级工程师彭云彪2人入选中国工...
2025-08-26 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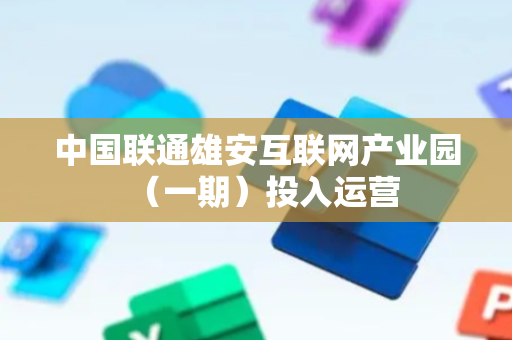
中新网雄安8月25日电 (谌诗雨 韩冰 作为雄安新区启动区市场化疏解项目之一,中国联通雄安互联网产业园(一期 25日正式投入运营。 中国联通雄安互...
2025-08-26 0

【来源:无为发布】喜报在刚刚落幕的2025年安徽省质量管理小组活动交流会暨成果发表赛上,由无为市工信局推荐的国网无为市供电公司两项QC成果参赛,从来自...
2025-08-26 0

反内卷的风,正在吹遍各行各业。比如,快递。如果你在广东做电商,你会发现,8月5日起,那个“8毛发全国”的时代,似乎要结束了。申通、圆通、中通、韵达,已...
2025-08-26 0

亲,这款游戏可以开挂的,确实是有挂的,很多玩家在这款游戏中打牌都会发现很多用户的牌特别好,总是好牌,而且好像能看到-人的牌一样。所以很多小伙伴就怀疑这...
2025-08-26 0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