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07-28 0
17世纪以来,解析几何崛起,人们习惯用坐标来描述空间。但这套方法有个根本问题:坐标系统是人为的,几何对象是客观的,两者之间如何脱钩?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一个向量的长度,在不同坐标系下应保持不变;一条曲线的切线方向,旋转坐标不应该改变它的几何含义。
于是问题来了:哪些表达式在坐标变换下“不变”?哪些是“伪对象”?
答案不能靠直觉,必须靠结构。
这时,数学家开始考虑:如果一个量在不同坐标系中变化,但其整体结构保持一致,那就说明它是“几何不变”的。最早的尝试是对向量、矩阵、线性变换做出系统描述,但这还不够。
因为几何中出现了越来越多多指标对象,比如曲面的第二基本形式、应力的分布函数,它们不再是简单的一维量,而是需要两个、三个甚至更多坐标指标来定位。
单靠向量、标量已无法表达这些结构。坐标变换也不再只是简单的旋转平移,而是任意映射下,变量如何重新“排列组合”。
这种需求,就是张量的出发点。
张量的核心,不是它有几个指标,而是它在坐标变换下怎么变。
但这个抽象概念并不是先由数学家提出的,而是由物理需求逼出来的——最早是在材料科学。
19世纪初,张量尚未成名,物理却已经先用上了它的“雏形”。
1822年,柯西在研究弹性体内部的力学平衡时,遇到了一个难题:如何描述物体内部任意一点处,朝任意方向作用的力?
靠向量不行。因为作用力的方向是一维,但接触面的方向也是一维,两者的组合变成了二维依赖结构。换句话说,要描述“朝 i 方向的力作用在 j 方向的面上”,需要两个指标。这就是“应力张量”最早的数学雏形。
柯西因此引入了一个 3×3 的矩阵,也就是今天所谓的二阶张量,表示任意方向上的面,对应任意方向上的力。
重要的不只是这个矩阵,而是这个结构满足一个核心逻辑:它在旋转坐标系时会跟着变,但变法是有规律的,最终计算结果(比如合力、能量密度)不变。
这就是张量观念的萌芽:对象本身在不同坐标下“变脸”,但物理量不动。
柯西没有发明“张量”这个词,但他第一次构造了一个物理意义上必须具有两个指标的量。这是从向量到张量的关键一跳。
在他之后,弹性理论、连续介质力学、电磁张量等纷纷开始使用这类结构。张量不是从数学中生出来的,而是从工程中逼出来的。
然而柯西关心的还是具体的力和平衡问题。他没有也不需要系统建立“张量变换律”。
1854年,黎曼在一篇题为《论几何的基础》的讲座中,扔出一句划时代的话:
几何的基础应建立在量与量之间的可度量关系上。
这不只是反对欧几里得几何,而是引入一个根本性转变:空间不是预设的,几何由内部的度量结构决定。
他提出:在一个任意曲面的任意一点,长度、角度、体积等几何量,都应由一个叫作“度量张量”(metric tensor)的东西来定义。这个对象——我们今天写作 g_ij——就是现代张量理论的正式起点。
它有两个指标,告诉你:在该点,坐标方向 i 与方向 j 之间的“度量关系”是多少。
更重要的是:它不是坐标赋予的,而是空间本身的“本地属性”。
这就是所谓的内蕴几何:不再依赖把曲面嵌入三维空间看弯曲,而是直接在曲面自身上定义“测量规则”。
从此,曲率、长度、体积等几何量,统统都被还原为对 g_ij的计算。黎曼本人还提出了今天被称为“黎曼曲率张量”的雏形,虽然他没有写下完整公式,但框架已经具备。
他没有叫它“张量”,但他给出了最早的、具有清晰几何含义的对称二阶张量,并且指出:它的变换方式决定了它是不是“真正的几何对象”。
如果说柯西的张量来自物理结构的多维依赖,黎曼的张量则来自几何结构的自洽性需求。
这时张量还只是个“方法”,不是一个“体系”。它的计算规则、导数推广、坐标变换律都还没建立。
有了黎曼度量张量,几何不再是画图,而是做计算。
但一个新的问题马上出现了:
如果张量是几何对象,那我们能不能对它求导数?
换句话说,张量场的“变化率”还能是张量吗?
答案是:不能直接求偏导数。
因为张量的变换规则非常特殊。你直接对它求偏导数,不会再得到一个“按张量规则变换”的对象。也就是说,普通导数不能保持张量性。
这时候,克里斯托费尔在1869年引入了一个关键概念:协变导数(covariant derivative)。
为了让张量在不同坐标系中求导后仍然“像张量那样变”,他引入了一组修正项——这就是今天我们熟知的克里斯托费尔符号(Christoffel symbols),记作
这些符号本身不是张量,但用来纠正偏导数的不变性问题。加上它们之后,导数操作才恢复了张量结构。
这一步彻底打开了张量分析的大门。
从此之后:
这也标志着:张量不再只是个多指标量,而是构成可微几何结构的基本语言。
克里斯托费尔虽然是做几何的,但他建的这套微积分系统,直接被后来的引力理论、规范场论、现代微分几何全面继承。
他没有发明“张量”这个词,但他给出了“如何运算张量”的全部规则框架。
这个词的正式确立,则来自两个意大利人。
到了19世纪末,张量的雏形已经具备:有了多指标对象(柯西),有了变换不变量的思想(黎曼),也有了正确的导数定义(克里斯托费尔)。但这些都是“散件”。
要把这些散件组装成一套可复制、可教学、可编程的数学语言,还差临门一脚。
这一步,由意大利数学家里奇(Gregorio Ricci-Curbastro)完成。他在19世纪90年代系统整理了所有前人成果,创建了一整套以“坐标无关”为核心的计算体系,他称之为:
“绝对微积分”(calcolo differenziale assoluto)
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把张量作为一等公民登上数学舞台,不再只是“多指标表格”,而是构造几何、力学、物理规律的通用语言。
他的学生——列维-奇塔(Tullio Levi-Civita)——将这套语言进一步优化和推广,加入了现代记号、更加系统的分类,并写成教材。他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引入了“张量变换律”作为定义标准:
凡是在坐标变换下按特定规则变化的多指标对象,才配叫“张量”。
这套标准一经确立,就像编程语言的语法规范一样,为后世无数几何、物理理论打下了语法基础。
到20世纪初,张量已经拥有:
但这套语言还停留在数学圈子里,没掀起大风浪。
直到爱因斯坦在1915年将其引入引力理论,张量才成为物理学中不可动摇的基础语法。
1915年,爱因斯坦站在普鲁士科学院讲台上,提出广义相对论。他没有从实验出发,也没有直接从几何构造,而是从一个极其大胆的思想出发:
物理定律的形式必须在所有参考系下保持不变。
这叫广义协变性。
问题是,用什么语言能保证“所有参考系下形式不变”?经典力学不行,矢量形式也不够——只有一套东西具备这个能力:
张量。
爱因斯坦直接引入了张量分析语言,把引力重新定义为“时空弯曲”,并用度量张量 g_μν 来描述时空结构。这个度量不再只是距离的计算器,而是决定光线如何传播、物体如何下落的物理结构。
他的核心公式:
两边全是张量。左边是空间的几何,右边是能量与动量的分布,整个宇宙的动力学就浓缩在这一张量等式中。
张量,从此脱离了数学的边缘地位,成为理论物理的“主语”。
但故事没有结束。狭义相对论也需要张量语言来表达洛伦兹协变性。量子力学和场论随后也发现:如果你想让局域对称性成立,张量结构必须内嵌进去。
张量,变成了物理的普遍语法。
爱因斯坦在1905年提出狭义相对论,最初只用到了简单的代数与坐标变换。但很快,物理学家发现:要将它写得更优雅、更通用,尤其是让它能扩展到场论,就不能只靠坐标公式——必须用张量语言重写一切。
狭义相对论的核心是:物理规律在洛伦兹变换下形式不变。
张量天生就适合干这件事。因为张量的定义本身就是:在任意坐标变换下按规则变化,从而保证整体表达保持结构不变。这正是“协变性”的含义。
于是,物理学开始以张量为基本单位,重写经典力学和电磁学,麦克斯韦方程在这个新语言下变成两条张量方程,简洁、对称、自动协变。
没有张量,你就无法说清什么是真实、什么是伪量,什么是标量场、什么是矢量场,什么能参与作用,什么是数学产物。
张量语言的引入,还为后来的量子场论提供了结构模板。你想让一个场是玻色子?那它必须是某种对称张量;你想让它是费米子?那你必须从旋量这个张量的“子种类”中选取。
接下来,这种结构进入量子时代,与对称性、群论、规范性联手,成就了现代物理最深的结构。
到了20世纪中叶,量子力学与相对论融合成了量子场论(Quantum Field Theory, QFT)。这时张量不再只是表达物理量的容器,而成为整个理论结构必须服从的框架。
核心原则是:
物理规律必须在局域对称性(规范对称性)下保持不变。
简单说就是:你可以在每一点自由地“旋转”内部自由度(如相位、色荷、味道……),但物理不能因此改变。这种局域旋转不是几何意义上的旋转,而是抽象空间(李群)中的对称变换。
这时候,张量语言再次登场,不只是坐标变换的“工具”,而是群表示的承载体:
你想让一个量“参与相互作用”,那它就必须是群的一个表示;你想让这个表示能写进拉格朗日量,那它就必须变换成张量形式。
连最核心的物理对象——拉格朗日量、作用量、能动张量、流密度、散度项……都必须是张量或张量密度。
更关键的是,张量给了我们计算“可观测量”的最短路径。因为你不知道自然的“本体”是什么,但你知道它必须在变换下给出不变预测,而这正是张量最擅长的事。
从规范场理论中,我们看到一个结构性事实:
张量是连接对称性与相互作用的最小语言单位。
如果没有张量,你没法让对称性“落地”,也没法构造作用,也就没法预测粒子如何交换。
接下来,数学家进一步从张量出发,构造更抽象的工具——丛、纤维、李代数表示空间。张量又一次被“升维”。
到这一步,张量已经是坐标变换下的不变量表达、物理对称结构的载体。但在更高层次,数学家开始问:
张量为什么“变成这样”?它们的变换规则背后有什么更深的结构?
这时张量被推进到了更抽象的层级——丛理论(fiber bundles) 和 李群表示。
李群视角:在物理中常见的“对称性群”都是李群(连续可微的群结构)。张量可以被视为李群在流形上的表示,是群作用下的场。这使得张量的“变换规律”不再是经验总结,而是李群表示论的直接产物。
举例:
丛理论视角:张量场不是“函数”,而是赋值在流形每一点上的线性结构,本质上是丛(bundle)上的截面。
这意味着,张量不只是“一个数学对象”,而是被整个空间的拓扑和几何结构所支配的局部实体。
更进一步,张量场之间的关系、平行传输、联络(connection)、曲率张量等,全部可以在丛上自然构造——这就是现代微分几何的基础结构。
也就是说:
张量不仅描述了空间中的对象,它们本身就是空间结构的表达。
在规范引力理论、弦论、非交换几何中,张量结构仍是核心。即使在极抽象的范畴论框架下,人们也往往要先“张量化”对象,才能定义范畴之间的态射。
但回到实际世界,它也没有脱离工程和应用。数值模拟和AI时代,张量又一次变身,成为运算主角。
进入20世纪中后期,随着计算机的普及,张量理论从抽象几何的高空,落到了数值模拟与工程计算的地面。
工程师、材料学家、气象模型师不关心协变导数和纤维丛,但他们天天面对应力张量、惯性张量、弹性模量张量、各向异性材料的响应张量。
这些张量不再是无限维流形上的场,而是离散网格上的有限维数组,本质上是矩阵或更高阶数组——这也是今天所谓“张量运算”的实际意义:
在编程世界里,“张量”通常就是带维度的多维数组,加上“如何变换”的规则。
这种“弱化版张量”,虽然远离黎曼几何,却保留了两个核心:
在流体力学、结构仿真、地震波模拟、航空材料分析中,张量场(尤其是二阶对称张量)作为模拟输入和输出,成为基础运算单位。
与此同时,线性代数的发展也开始以“张量积”为核心运算操作,把向量空间的组合结构看作最基本的构造手段——不仅方便编码,也适用于物理建模。
尤其是在有限元分析(FEM)与有限差分法(FDM)中,张量形式的物理律表达,是构造数值格式的语言基础。
工程上的“张量”不必追求全协变性,但一旦进入曲面力学或非线性弹性,就必须重新回到真正的张量变换律。
张量由此实现了从理论物理到工程数值的全链路穿透:既能表达弯曲时空中的引力,也能用于模拟风洞中的翼型结构。
而到了21世纪,它又一次在意想不到的地方重生——人工智能。
进入21世纪,张量在一个出人意料的领域“再就业”:人工智能。
现代深度学习框架——如 TensorFlow、PyTorch、JAX,甚至名字里都直接带了 “Tensor”——并不是在卖弄高数,而是在告诉你:
整个神经网络本质上就是张量变换的流水线。
在这个语境中,张量通常指的是:
更进一步,高阶张量分解(tensor decomposition) 成为模型压缩、表示学习、参数高效化的重要工具。
比如 Tucker 分解、CP分解、张量网络(Tensor Networks),这些概念最早来自量子多体物理,如今又在机器学习中发光发热。
AI研究者逐渐意识到:
不理解张量结构,你写不出有效的模型;不了解张量变换,你调不动高效的训练。
虽然在AI中,“张量”这个词常常被当作“带维度的数组”来用,少有人考虑它是否满足坐标变换下的协变性——但它仍然继承了“结构有维、行为有律”的核心精神。
于是我们看到,从19世纪的黎曼几何,到20世纪的相对论,再到今天的图像识别与自然语言处理,张量完成了一次跨越三层学科的语言迁移:
从几何语言 → 到物理语言 → 再到机器语言。
但它仍然面对一个哲学老问题:张量究竟是现实的结构,还是人类书写现实的方式?
张量如此强大,几乎无所不包——从引力场到神经网络,从黑洞结构到图像识别。但这也引出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张量到底“存在”吗?它是自然的结构,还是我们对自然的编码?
这不是学院派争论,而是一个决定你怎么看待整个科学框架的问题。
一种观点是实在论(realism):张量就像质量、电荷、时间一样,是自然界客观存在的一部分。
例如在广义相对论中,度量张量 g_μν 决定了光线怎么走、物体如何自由下落,它不是“描述”,而是“决定”物理行为的实体。
这意味着:
张量是自然的组织方式,我们只是发现了它。
从这个角度看,张量的变换律不是人造规则,而是宇宙的深层对称性在数学中的显影。
另一种观点是工具论/结构主义(instrumentalism/structuralism):张量是语言,是我们用来描述物理世界的“语法工具”。它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满足了一种强约束:
换句话说:
张量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们要求自然规律具有“坐标独立性”这一形式美。
在这个观点下,张量不是“真”,而是“方便”。就像我们选择用实数描述连续性,不是因为自然真的“用”实数,而是因为实数让我们可以表达足够多的物理过程。
还有一种观点介于两者之间:张量是一种结构映射:它不是实体,但它确实反映了自然中的结构关系。
它们不是自然本身,但它们像地图一样,成功地与自然之间形成了一种稳定对应关系。
张量已经成为21世纪理解世界不可绕开的核心语言。
相关文章

金融界2025年7月23日消息,国家知识产权局信息显示,卧龙电气驱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龙能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取得一项名为“光伏清扫机器人的控制系...
2025-07-28 0

AI手机与服务体系的重新定义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2025年国家发展战略中明确指出了AI手机概念的重要性。这意味着移动终端和服务体系将经历一次深...
2025-07-28 0

7月26日,2025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WAIC)在上海世博中心正式启幕。大会由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科技部等七部委联合中科院...
2025-07-28 0

中国青年网延吉7月27日电(记者 高蕾 实习生 李苏玲)在长白林海苍翠欲滴、图们江畔生机盎然的盛夏时节,第五届中国新电商大会核心分论坛——“可持续发展...
2025-07-28 0

作者 | Matt Foster译者 | 明知山一项最新的研究 对 AI 工具能够加速软件开发的普遍认知提出了挑战。METR 的研究人员针对经验丰富的...
2025-07-28 0

金融界2025年7月26日消息,国家知识产权局信息显示,白鸽磨料磨具有限公司申请一项名为“一种基于3D打印的高精度CBN成型磨砂轮及其制造方法”的专利...
2025-07-28 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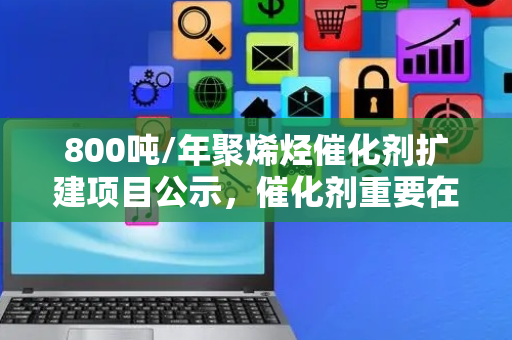
7月14日,沧州利和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年产800吨聚烯烃催化剂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第二次信息公示。在现代化的今天,各种人造纤维、人造树脂和塑料制品...
2025-07-28 0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