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好:这款游戏可以开挂,确实是有挂的,很多玩家在这款游戏中打牌都会发现很多用户的牌特别好,总是好牌,而且好像能看到-人的牌一样。所以很多小伙伴就怀疑这...
2025-09-09 0
9月4日,美国华盛顿,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白宫国宴厅与科技界领袖共进晚餐。特朗普表示,他将“很快”对半导体进口征收关税,但将豁免苹果公司等已承诺增加在美投资的公司的商品。视觉中国供图
9月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科技企业高层共进晚宴前向媒体表示,美国政府将对未在美国境内设立或规划生产设施的半导体企业进口产品征收较大幅度关税,以推动相关企业在美投资建厂。特朗普称:“我们会对那些没有在美国设厂的公司征收关税,这一关税不会特别高,但相当可观。”他同时强调,已在美国建厂或已承诺未来投产的企业可获得豁免。此前,8月7日,特朗普曾提及关税水平可能最高达到100%。截至目前,有关关税实施的具体细节尚未正式公布。
特朗普表态后,半导体行业多位领军人物迅速作出回应。德州仪器首席财务官拉斐尔·利萨尔迪指出,在加征关税的预期刺激下,所增长的订单量仅属短期现象,难以带来持续性需求;英飞凌亚太区总裁蔡士钊强调,关税政策令全球半导体行业面临高度不确定性,企业难以制定长期战略;荷兰光刻设备巨头阿斯麦首席执行官傅立格则警告,对关键制造设备加税将直接推高生产成本,并削弱全球供应链的稳定性。
“胡萝卜+大棒”:关税与补贴推动芯片回流
美国政府对进口半导体加征关税的政策核心,在于推动跨国企业在本土建设晶圆厂,回流相关制造产业链环节。这一策略延续了其一贯的“胡萝卜+大棒”思路:一方面通过高额关税制造外部压力,迫使企业重新评估在美布局;另一方面,则以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和政策承诺提供吸引力。
支撑这一框架的核心法律是2022年签署的《芯片与科学法》。该法案提供总额约527亿美元的联邦支持,其中390亿美元用于制造业投资补贴,约132亿美元用于研发与人才培养,另配套25%的投资税收抵免,涵盖在美新建或扩建的半导体产能。白宫在政策解读中明确强调,这一举措不仅仅是产业政策,更是“让美国再次伟大”执政理念在先进制造领域的延伸,其战略目标在于重建核心产业基础,提升供应链韧性。
在传统补贴之外,美国近期迈出直接资本介入的特殊一步。2025年8月22日,白宫宣布将把部分尚未拨付的CHIPS资金和其他联邦项目资金“股权化”,注资约89亿美元取得英特尔约9.9%的股份,整体交易规模接近110亿美元。根据官方声明,此类股权为“被动投资”,美国政府不会取得董事会席位,但其象征意义与战略目标十分明确:通过直接入股这一全球芯片巨头,确保本土高端芯片制造产能恢复,并向市场释放长期政策承诺。
英特尔方面表示,该资金将有助于支持其代工业务发展和在美扩产,尤其是亚利桑那和俄亥俄新厂的建设。路透社评论指出,这一案例标志着美国半导体产业政策由传统的“补贴—贷款”模式转向“直接持股”,显示出政府在保障产业安全方面的强烈决心。与关税形成互补,这一举措既强化了财政激励的力度,也通过股东身份提供了更深层次的政策约束力。
由此可见,美国推动半导体产业回流的手段正形成一个多层次的“组合拳”:关税作为“硬约束”,补贴与税收抵免构成“软激励”,而直接持股则提供了更具长期性的产业介入路径。这一政策体系的共同目标在于缩小本土与亚洲制造中心的成本差距,并在供应链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确保关键技术不受外部风险干扰。
“空心化”与回流成本:100%关税的保护力几何?
美国半导体产业的“空心化”已有三十余年历史。根据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SIA)数据,1990年美国本土晶圆制造产能占全球约37%,而到2020年这一比例已降至12%左右。尽管美国在芯片设计、EDA软件和关键设备领域仍保持领先地位,但在资本密集度最高的晶圆制造环节,美国已不再是全球主力。由此导致的局面是,即便美国企业在研发端掌握高利润环节,其生产端却高度依赖亚洲地区,供应链安全问题日益引发战略关切。
从利润角度看,半导体行业并非绝对暴利。以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为例,其2023年毛利率为54.4%,2024年回升至56.1%。这一水平虽高于多数传统制造业,但其中相当部分被高额的研发投入、设备折旧和产能扩张所消耗。台积电亦多次强调,随着在美国、日本、欧洲等地新厂建设推进,其海外生产线成本远高于台湾本部,未来数年将导致整体利润率下滑2—3个百分点。换言之,将相同工艺迁移至美国,势必压缩企业利润空间。
关于成本差异,多份研究给出了相近结论。波士顿咨询公司(BCG)与SIA的联合报告指出,在缺乏同等补贴的情况下,美国新建晶圆厂的十年总拥有成本(TCO)比台湾地区、韩国、新加坡高出约30%,比中国大陆高出约50%。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曾公开表示,在美国生产的相同芯片,成本较台湾地区高出50%以上。近期,AMD首席执行官苏姿丰也在公开场合透露,未来从TSMC亚利桑那工厂采购的芯片,成本将“比台湾地区制造贵5%到20%”。尽管不同来源的估算存在幅度差异,但均指向同一共识:美国本土生产存在显著溢价。
在此背景下,美国政府提出对未在美建厂的半导体产品加征最高达100%的进口关税。若暂不考虑这可能是特朗普团队惯用的谈判策略,仅以此数值进行测算,则问题在于:如此高的关税是否足以对冲回流带来的成本劣势?若按最低估算,美国生产溢价约为5%—20%,那么100%的关税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差距;但若依据BCG或张忠谋提出的中高区间(30%—50%),100%的关税仍不足以改变企业的成本劣势。换言之,这一关税政策在短期内难以对本土芯片制造形成实质性保护。
更值得注意的是,高关税可能带来多重“副作用”。首先,下游ICT设备制造商(包括服务器、智能手机、个人电脑厂商)将直接承担上游成本上升压力,最终可能传导至消费端,削弱美国整机厂商的国际竞争力。其次,由于美国尚未建立完整的上下游协同生态——例如材料、封测、化学品等供应链高度集中于亚洲——即便本土晶圆厂建成,配套不足也将进一步推升运营成本。
因此,100%的关税更多具有象征意义和谈判筹码属性,而非具备足够实际保护力的经济工具。若要真正缩小成本差距,美国必须依赖财政补贴、投资税收抵免以及政府采购等多重政策手段协同发力。
总体来看,美国半导体“空心化”并非单纯的短期成本问题,而是由产业集群效应与完整产业生态长期演化形成的系统性优势所致,难以简单复制。100%的关税难以弥补这一系统性差距,产业回流在短期内无法依靠市场力量自发完成。未来美国重建本土产能的路径,将继续依赖于持续的财政补贴、政策性投资与战略采购支持,而非单一的关税壁垒。
经济逻辑的边界与地缘政治的主导
美国推动高端芯片制造业回流的核心逻辑,并非基于纯粹的经济效率,而是服务于以供应链安全和大国战略竞争为导向的地缘政治目标,经济政策在此框架下做出让步。过去三十年的产业外迁,是全球化分工体系下基于成本优势与产业生态协同的自然结果,而美国本土在劳动力、基础设施和产业链配套方面的比较劣势,仍是制约制造业回流的关键瓶颈。
即便在补贴与减税政策加持下重建本土产能,单位成本上升与利润率被动下移仍是大概率事件。企业端只能通过长期规模化、自动化以及本地配套完善来逐步缓解压力;政府端则需在可预期的财政支持、稳定的税制环境与高效的监管审批之间作出承诺。
就当前态势而言,美国本土先进制造业产能的恢复将持续依赖财政激励与一定程度的关税、采购保护机制。本土产业结构的深度转型与可持续增长,仍有待时间检验与政策连贯性的支撑。
(作者:薛子敬,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研究员)
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
相关文章

您好:这款游戏可以开挂,确实是有挂的,很多玩家在这款游戏中打牌都会发现很多用户的牌特别好,总是好牌,而且好像能看到-人的牌一样。所以很多小伙伴就怀疑这...
2025-09-09 0

亲,这款游戏可以开挂的,确实是有挂的,很多玩家在这款游戏中打牌都会发现很多用户的牌特别好,总是好牌,而且好像能看到-人的牌一样。所以很多小伙伴就怀疑这...
2025-09-09 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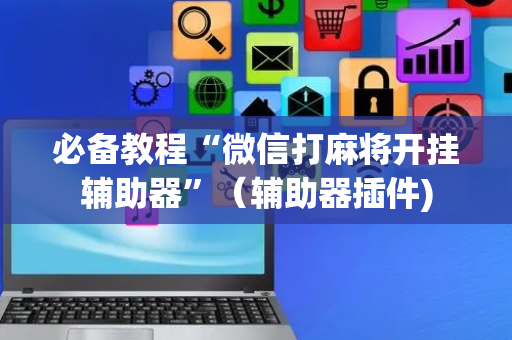
亲,这款游戏可以开挂的,确实是有挂的,很多玩家在这款游戏中打牌都会发现很多用户的牌特别好,总是好牌,而且好像能看到-人的牌一样。所以很多小伙伴就怀疑这...
2025-09-09 0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