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需打开直接搜索微信:本司针对手游进行,选择我们的四大理由: ...
2025-09-08 0
01
引子
最近在腾讯内部的会议上,在讲述游戏业务现状的时候,腾讯高级副总裁马晓轶(Steven)聊起了曾经的困惑:
"今年大家都说我们业绩好,产品也不错。但有一件事很有趣:我们这两年表现得好的新项目,立项或者投资都发生在2021年左右,比如《三角洲行动》《黑神话:悟空》。"
回忆完这一切,他对着面前的几家媒体笑了笑:“但要知道,在2021年之后的很长一段日子,在座的各位都在问:腾讯是不是不行了?是不是犯了很多错误……不是怪你们的意思,你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
"那怎么办呢?这就像是一款格斗游戏,已经按下了出拳键,你也没法收回来,那只能等。一直等到2024年,突然之间一切都变好了。但其实从21年按下这个按钮,我们没有什么改变。"
腾讯游戏没有改变的到底是什么?他们又真的毫无改变吗?看完这篇采访,或许你会得到答案。
02
成功率
在科隆游戏展期间,包括游戏葡萄在内的多家媒体和马晓轶在莱茵河畔吃了一顿Brunch(早午饭)。过去几年,葡萄君也曾采访过几次Steven,但可能得益于这一次的形式,今年的交流氛围格外放松。

腾讯集团高级副总裁马晓轶
他几乎回应了媒体们的每一个问题,不管是正面提问,还是旁敲侧击,包括一直以来外界对腾讯的各种质疑和误解:成本高、没耐心、抓机会、赛马……但最令他头疼的并不是这些,而是大家对于腾讯游戏成功方法的成功学式揣测。
"媒体总是喜欢找一个充分条件,说只要做到了这个,就成了。但更多情况下,可能是要先做到10个必要条件,你才有抽奖的资格。而且就算有了资格,最高的中奖率也可能只有30%。"
在他看来,成功没有什么充分条件,只有必要条件。就算叠加各种资源、能力和IP,但对一款新游戏来说,成功率能做到30%就到顶了。
一名腾讯游戏内部人士称,在这位总办成员的话语体系中,最高频出现的关键词是「提升成功概率」,其次是「建设性」、「积累」、「条件」。如同我们之前所说,他所关注的,不是下一个爆款在哪儿,而是如何更好地设计机制、分配资源,提升下N个爆款诞生在腾讯体系的概率。简单来说,他们关注的不是成功,而是成功率。
在外界看来,这几年腾讯正在变得更加耐心。但Steven认为,大家对此依旧存在误解:“其实我们一直挺有耐心的。”
在他的描述当中,腾讯一直希望做好成功的必要条件,帮助更多团队把成功率提高到30%,让大家有一次又一次冲击长青的机会。
“如果每次中奖率只有30%,你可能得抽4次才能中1次。所以我会和很多团队说,不是我们不愿意花钱,而是如果活得足够久,能迭代很多次的话,你成功的概率会更大;你不能说我这次100%能成功,然后孤注一掷。”
不过,虽然「提升成功概率」的逻辑没有改变,但腾讯也在不断观察外界的信息,反思认知,调整机制。用Steven的话说:“我们一直在转型。”
比如,曾经他认为绝大多数团队都应该尝试GaaS。但最近他正在反思,做出长青的GaaS产品,可能需要“一章一章打过去”。如果把目光放长远,把一款买断单机当做验证美术、玩法、故事的垂直切片,那完全可以支持团队去做单机。
03
一望无际的平原
但如果成功学并不靠谱,我们应该相信什么?
对规律的观察、对方向和必要条件的论证、积累经验的技巧、对过去四十年玩法脉络的梳理……听上去很抽象,但这些反而可能是腾讯游戏最推崇的东西。
和Steven聊过几次后,我偶尔会在脑海中想象一幅画卷——
全球游戏市场好像一片一望无际的平原,平原上是35亿游戏用户。多年以前,天才在高山之上创造出了惊艳的玩法,它们顺着水流一路奔流,被后来者汲取养分,再创造,然后开拓出更多被后人称作细分品类的支流。

在流水两岸,懂得利用流水的人们繁衍生息,建造了大大小小的聚落。有的聚落曾经很庞大,但却耐不住风吹日晒,最后消逝在岁月当中;有的聚落虽然狭小,但凭借对于品类和玩法的独到理解,在这一段支流上建立了一座堤坝,甚至圈住并命名了这一小段河流。
有的时候,大家也会共同眼红某段河流的肥美,都想修一座属于自己的堤坝,于是产生冲突。但如果从天空当中向下俯瞰,你会发现和广阔的平原相比,这一小段河流实在微不足道。只要不刻意凑在一块,你就和别人的成败没有太大关系。
作为普通人,我们当然很难,也没有必要时刻保持这么宏大的视角。不过在担忧游戏行业未来,抱怨增长见顶、竞争加剧的时候,偶尔这么想一想,心情还是会开阔许多。
我采访过很多游戏公司的老板,但诸如唤起胜负欲之类的采访小技巧,在对话Steven时一般是失效的。
一位腾讯游戏内部人士称,在Steven的话语体系里,很少会出现「对手」或「竞争」。"商业竞争的关键是认知,以及认知有没有配套的机制和实践,而不是对手。他给人的感觉是:我自己还有好多东西没忙过来,盯着你看干什么?”

科隆游戏展期间,Steven在体验游戏
在他眼中,腾讯游戏还有很多很多事要去做。比如全球范围内,符合他们长青标准(年流水超过40亿,且季度平均DAU超过500万的手游,或超过200万的端游)的游戏约有70款,其中14款(财报数据)来自腾讯,腾讯的投资公司还有8款,但除此之外,他还希望看到至少30个候补选手。
这些候补选手,可能都是自己品类的第一、第二名,在平原上拥有一段支流、一块稳定的聚落。就像「搜打撤」一样,他们所处的支流,可能总有一天会因为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变得更加辽阔。
全球前三的游戏厂商,只有腾讯没有平台级的硬件设备,它能做,或者说一直在做的,就是用认知、机制、有专业价值的支持,搭建或者连接一个又一个的聚落,构筑不断涌现好游戏的生态——想到这里,我感觉像是打开了一局永无止境的《文明》。
正如Steven所说,腾讯游戏的转型和迭代将继续下去,但有了这几年起起伏伏的经验,他们对于自己摸索到的产业规律多了一份笃定。“这个行业的一个周期可能就是4-5年,要想象我们在玩一款延迟很高的格斗游戏。”
以下为多家媒体与Steven的餐叙摘录,为方便阅读,内容和顺序有所调整。
04
单机买断:鼓励扶持,
努力定义一个类型
媒体:逛完今年的科隆游戏展,你有什么印象深刻的点吗?
Steven:美国公司来得比较少,欧洲本土游戏也相对少一点。反而东亚板块,十分活跃。
媒体:是因为欧美的3A游戏行业遇到问题了吗?
Steven:游戏行业是有周期的。在90年代,日本一度领先欧美,但在2000年左右,因为坚持他们的手艺活儿,没有及时拥抱游戏引擎;之后20年,欧美一度有了统治级的力量,但他们不少制作人,小瞧了GaaS和平台化的力量,到2021年左右,开始出现一些问题。
我之前说过,因为买断制是预先付费,有的团队会在前1-2个小时投入50%的预算,让游戏看起来非常有吸引力,熬过玩家能退款的时间。但现在全球最顶尖的游戏,可能每款都能让玩家玩1000小时以上。相比之下,只做2个小时的投入,这个理念可能是不对的。
媒体:所以是不是就不该做买断?
Steven:倒不是买断的问题。我们在内部都有讲,公司一点都不反对大家做买断制游戏。大家也有看到,最近我们有很多类似单机的探索性项目出现。
游戏行业的竞争激烈到大家难以想象。每年Steam上有约1.9万款PC游戏,手机上有超过6万款移动游戏,成功的能有多少?以过去一年为例,跨过“长青游戏收入线”的新游戏预计只有6款:《绝区零》《鸣潮》《恋与深空》《Helldivers 2》(绝地潜兵2)《黑神话:悟空》《三角洲行动》。这6个团队,在自己的领域做得都挺久。

在这个行业,想一步就成功太难了。以前我们会对欧美的工作室说:“你们应该做GaaS化”,这是对的,因为大部分的长青游戏都做了GaaS化。但这是一个End Game(终局),按照游戏的说法,你得一章一章打过去。
所以在内部,我们能接受大家拆解这个过程,花几代时间,最终做到长青。这里面每一步的挑战都很大,做一款PC单机可能相对还简单一些;做多人对战,做跨端,这都是指数级上升的难度。
反过来说,想实现长青,你要把故事和玩法打磨得非常好。但如果前期就已经做得这么复杂,这么难,成本又特别高,你该怎么打磨游戏?
媒体:所以腾讯内部所有项目的终局都是GaaS(Game as a Service),单机只是其中的一个步骤?
Steven:应该说终局是长线运营。游戏已经从单纯的内容,转变成了很多人的生活方式。理论上说,任何一款做得好的游戏,都是因为做了很多很对的事情,定义了某个游戏类型。这样玩家就会持续去玩,你也要不停改进你的游戏,增加新的内容。
就像很多人看到一款动作游戏,就会说它是魂like,因为它定义了这个类型。我们对内部团队也会说,虽然很难,但希望「定义一个类型」是大家长线的目标,因为这样你会有很强的生命力。哪怕有一天要停下来也没关系,只要能想到应该怎么做,就还是能再做起来的。
媒体:这里有一点很反常识:一个做过很多年GaaS的团队,如果要花几代时间做单机,这个账会不会算不平(亏钱)?
Steven:做单机也不见得亏钱。整个市场在好起来,新一代玩家的付费意愿也在好起来。如果质量能做得足够高,其实还是有机会的。
05
长青:重要的不是成功,
而是提升成功率
媒体:在你看来,腾讯、甚全球游戏市场到底能容纳多少款长青游戏?70款会不会已经是我们的上限?
Steven:不会,因为市场真的很大。现在全球应该有35亿玩家,用玩法、背景(题材)、难易度等各种维度去切,可以切出无数的细分类型。就看大家能不能定义各自的类型,让自己稳住。
就像大家说腾讯已经有这么多射击游戏了,怎么还在做?但我们内部算了算,射击游戏占了全球35%的市场,但中国这个数字只有大约20%——后者应该还能再涨近一倍吧?也许有一天它会饱和,但那一天还比较遥远。
媒体:你们是否有办法在一款游戏出现之后,判断它有多少概率成为长青游戏?
Steven:其实没有,我们希望每款游戏都能做到足够大,但这里面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就算不断努力,叠加资源、能力和IP,但对一款新游戏来说,成功率能做到30%就到顶了。
所以一款新游戏能不能成为「大学生」有很多不确定性。我们当然会按照「大学生」的方向培养及寻找团队。但大家能不能在今年就考上大学?还是要抱一个客观理性的态度:今年考不上也没关系,明年,或者未来,还可以再考。
媒体:那其余70%的不确定性可能是什么?某种社会思潮或者文化风向?
Steven:还有用户的口味、期待,以及玩法的难易等等。
用户的满意度,永远是他们实际上手玩到的东西再减去期待值。从这个角度,你不能把期待值拉得太高;但如果大家都不期待,那就没人玩你的游戏。
所以,光是期待值这一个动态指标就很难调整。你说有没有什么数据或公式?真的没有,只有试很多次才能试出来。
媒体:如果延续这个问题,《三角洲行动》那70%的要素可能是什么?
Steven:昨天我和Leo(天美J3负责人)聊,我们会认为这里有两个很重要的决策。
第一个决策是PC First。在2019年之前,中国游戏市场就是移动游戏市场为主,我们做的所有游戏都是先瞄着移动去的。但2023年,他们决定先做PC端,做到满意再porting(移植)到手机上。
这个决定让游戏的制作水准提升了很多个(量级),而且,现在PC市场也变得足够大——年轻一代起来了,PC的制作技术成熟了,刚巧各方面都ready了。
第二个决策,说起来也简单,就是团队觉得「搜打撤」不只是一个非常小众的hardcore(硬核)玩法,它还可以成为一个大众类型。
这两个决定,今天回头看都很容易、很明显。但放在2022、2023年,回到那个场景,你会发现决策还挺难下的。
媒体:如果把时间线拉长,一款长青游戏是不是再怎么迭代,都会慢慢落后于时代?
Steven:我不觉得一款游戏天生就该一路向下走。你看CF、DNF也一直都在迭代。这个版本的内容不够好,玩家是会离开。但只要你做出了好内容,他们还是会回来。
媒体:之前腾讯总办曾在财报电话会议中说,王者与和平团队的调整很成功。对于腾讯体系内的其他团队,你们也会直接推动团队调整吗?
Steven:工作室更多是独立决策。但开发者往往是孤独的,他们遇到的很多问题都非常难,而我们可以做的是打开他们的眼界,让他们知道别人怎么做。
比如Supercell,他们做出了长青游戏,玩家的需求很多,这很正常,但他们是一个小团队,小团队承接不了那么多需求,又担心扩大团队会丧失自己曾经的优势。于是我们说,我们邀请你们的管理层来我们这里交流一下吧,如果管理层还不够,那就邀请你们整个团队来深圳科兴,来跟其他大团队交流是怎么做的,正好我们内部也跟你们学习一下。

这样的交流持续了蛮长一段时间,在不断互相借鉴经验的同时,他们基于自身的战略思考,逐渐决定扩大团队,让小团队和大团队并行,创意孵化保持小团队,产品到一定程度后逐步扩大团队规模,实践下来,很多问题自然就解决了。
媒体:对于腾讯来说,追逐长青游戏会有什么坏处吗?
Steven:有一个坏处,可能是留给人才的副本太少了。
想培养最顶尖的人,就跟想练一个满级的号一样。如果没有足够多的副本,哪怕底子再好,上来roll出的点数再高,也很难成为最顶级。
为什么腾讯这么开放?可能因为我们允许大家出去刷一圈副本,最后我们也认你出去刷本的价值,让好的人才刷足够多的副本、做足够多的项目,这是发掘这些人、培养这些人最好的办法……
媒体:在你看来,长青是结果论还是方法论?
Steven:是结果。最终能定义品类的游戏,只要愿意通过不断的开发、运营满足玩家的需求,就有可能长青。
媒体总是喜欢找一个充分条件,说只要做到了这个,就成了。但更多情况下,可能是要先做到10个必要条件,你才有抽奖的资格。而且就算有了资格,最高的中奖率也可能只有30%。
为什么我们允许团队做迭代,做积累?因为如果每次中奖概率只有30%,你可能得抽4次才能中1次。所以我会和很多团队说,不是我们不愿意花钱,而是如果活得足够久,能迭代很多次的话,你成功的概率会更大;你不能说我这次100%能成功,然后孤注一掷。
06
耐心与机会:时代变了,
把握三个Right
媒体:在你的描述里,腾讯是一家很有耐心的公司。但在刻板印象甚至员工眼里,情况并不是这样。
Steven:这个大家有误解,我们其实一直挺有耐心的。
今天大家看到我们的射击很强,其实大家不知道,2008年CF上线后,2009年我们布局了多款射击游戏。在当时,中国有哪些团队敢投入这么多射击游戏?
媒体:这里面成功了几款?
Steven:可能只有《逆战》成功了,但我们还是一直在投入,直到今天。所以很多时候不是公司没耐心,而是公司要找到足够有耐心的团队。

逆战是腾讯少数的自研射击IP
如果立项的原因,只是说现在看到一个项目不错,我们也冲一个吧!这就没有意义。但如果你说,我希望射击游戏这样做,也许这一代不一定成,但我坚信它有机会,那可能我们反而愿意投入。行业里能获得很大成功的团队,大部分都有这样的坚信和坚持。
外部会觉得腾讯很看数据,但其实,我们更希望把KPI当作汽车上的仪表盘,让团队在开车的时候,知道自己在哪里,是什么状态,速度是多少,水温是多少。
媒体:那在决定一个项目是不是要做的时候,具体是谁来做这个判断?
Steven:往往是工作室的负责人。大家都说腾讯是大公司,但其实腾讯游戏是几十个团队组成的生态。我们希望工作室的决定千奇百怪,能帮助公司在不同的方向、品类取得长期成功。同时,我们也会提供我们的工具和激励,去帮助工作室做出更好的决策。
媒体:如何判断一个表现不好的团队是还在积累,还是应该调整?
Steven:最关键的指标有三个:
第一,Right Vision,团队要明确自己想定义的游戏类型。
比如说,我做射击,是因为我看到了市场上射击游戏有哪些问题应该解决,就像《Valorant》(《无畏契约》)研发团队当初觉得硬核射击同类产品节奏感不够强、不够现代、玩法比较单一、只追求单局胜负一样,然后他们觉得有办法做得更好,哪怕它不容易,需要做很久甚至很多代,那就是Right Vision。

第二,Right People。Right People不一定一开始就是成功的,但他们有自己的思考,有足够的感召力可以招到人来认同他们的理念,还有长期的信念,这样的团队就很好。
第三,Right Approach,要有好的工具,好的方法。就像最近大家忽然看到《湮灭之潮》《穿越火线:虹》《古剑》都很漂亮,那是因为我们用了UE5,而且后面还有很多项目会用UE5。
《穿越火线:虹》
事实上,2022-2023年,我们有过一次非常深入的讨论,认为UE5要明显强太多了,建议团队都转用UE5。像《沙丘:觉醒》也换了引擎,转是很痛苦的,但我们说,如果因为转引擎delay,我们愿意加钱,因为这是对的方向,最后项目延迟了一年,我们的预算也跟着涨了一年。类似这样的决定和支持,我们还有很多。
媒体:现在面对一个短期机会,你们怎么判断要不要做?
Steven:如果现在市场有产品做到了100分,那做个105分的产品快速进入市场,恐怕很难抓住机会。但如果说,我有一个想法,短期内能做到150分,长期来看能做到200分甚至更高,那就是好的。
媒体:这恐怕很难想到。
Steven:这个行业就是这么难。
媒体:曾经腾讯非常注重抓机会,现在你们没有那么强的执念了吗?
Steven:这里面有很多误解。为什么大家曾经对抓机会这么饥渴?因为中国游戏市场是从零开始的。
2014-2018年,整个市场有太多空缺的机会。很多人都抓住了机会,那时市场一片繁荣。但当市场成熟的时候,你会发现抓住机会的标准变得越来越高。如果你做不到100分,你就抓不住这个机会了。
媒体:现在腾讯还会特别鼓励赛马吗?
Steven:其实大家看到赛马这种情况出现,是有原因的,并不是说我们有意去推动大家赛马:
第一,我们所有工作室都是独立决策;
第二,过去一段时间,低垂的果实比较多的时候,大家总觉得只要抢一把,就有机会抓到手;
第三,如果抓到机会的回报很大,我们愿意花一些资源去重复投入。
在今天,我们还是不介意重复投入,团队的成功也需要很长时间的积累。如果大家都有积累,也都看好这个方向,那撞车也是正常的。
媒体:聊到机会,为什么你们押注了很久的SOC一直没有爆发?
Steven:SOC还处在很早期的阶段,就和曾经的“搜打撤”一样。它要解决很多玩法上的挑战,比如Survival(生存)压力给得太大,游戏很难持续;给得太小,又没什么意义了。
至于Open World(开放世界),昨天我们在Family Summit上也有很多讨论。理论上Open World应该有更大的自由度,但自由度一大,玩家又容易迷惑,于是就开始做引导。可一做引导,又很容易重复,甚至变成罐头了。
这样列了一下,SOC可能有十几个问题都没有解,可能要很多款、很多代产品一个个去解。但如果能解掉,那就是一个巨大的机会点。虽然说解题也很难,但总比没有方向乱摸要好。

腾讯旗下Funcom推出的《沙丘:觉醒》
07
AI:看好智能NPC,
更信奉涌现
媒体:腾讯在AI增效方面已经足够强了,但在AI原生玩法层面,你们能看到一些确定的方向吗?
Steven:和SOC一样,方向很确定,但路径没那么清晰。
比如AI可以做出很智能的NPC,但这里面有很多工程性的问题,比如长期记忆。在最理想的情况下,AI应该像你身边的朋友一样,能回顾和记住你和它所有的交互历史,但现在能记住3000字都要耗费巨量的算力。
想象一下,如果整个城市的NPC都有记忆,你都要通过谈话来获取信息,游戏会有多生动。这才是真正有Roleplay(角色扮演)的活的世界。可惜今天做不到,技术还不够。
媒体:那你们会不会通过一些研发机制,来牵引所谓AI原生游戏玩法的出现?
马晓轶:我们会做一些实验,但腾讯还是比较信奉涌现。我不觉得原生AI玩法是某个天才在楼上的办公室想出来的,它一定是成千上万的人在日常当中用出来的。所以我们会做三件事:
第一,我们会有中台的团队,不停尝试前期比较难,有技术和工程挑战的事情,在内部做研究;
第二,我们会推动所有的自研、发行、投资公司团队,每天想着法地去折腾AI,看看有没有我们没想到过的AI玩法涌现;
第三,让团队保持足够开阔的眼界。我们会经常组织大家找集团内部的AI团队,或者邀请外部AI公司来我们这里聊,看看哪家的AI做得比较好、比较有意思。
08
心态:
游戏行业周期越来越长了
媒体:和前些年相比,这些年你的心态有什么变化?
Steven:我对游戏行业周期的理解越来越长了。以前我觉得差不多是2-3年,但最近我发现这个行业的一个周期可能就是4-5年,要想象我们在玩一款延迟很高的格斗游戏。
在一次内部的会议上,我讲过一个现象:今年大家都说我们业绩好,产品也不错,但有一件事很有趣:我们这两年表现得好的项目,立项或者投资都发生在2021年左右,比如《三角洲行动》《黑神话:悟空》。所以今天大家看到的一些结果,都是因为2021年左右我们按下了一个按钮,然后等待一切发生。
《三角洲行动》
但要知道,在2021年之后的很长一段日子,在座的各位都在问:“腾讯是不是不行了?是不是犯了很多错误?”不是怪你们的意思,你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
那怎么办呢?这就像是一款格斗游戏,已经按下了出拳键,你也没法收回来,只能等。一直等到2024年,突然之间一切都变好了。可我们其实没有什么改变。
这件事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触动。这个行业的周期可能就是4-5年,因为这是一款项目决策的周期。以前我们每1到2年看一次未来的判断,只是中国游戏行业从零起步的特殊现象,不能把特殊的现象看作常态。
媒体:2021年最受外界挑战的时候,你们真的那么有战略定力吗?
Steven:其实当时我们内部有很认真地反复讨论,说我们要不要做内容向?但这个讨论没有解,因为还是有很多认知、能力积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拥有的。
媒体:你会认为在当下,腾讯依然处在一个需要转型,要努力扭转自己心态的阶段吗?
Steven:我们一直在转型。我觉得腾讯有一个好处:就是能比较客观地讨论自己哪些做对了,哪些做错了,做对的地方能不能再放大一点,做错的地方要不要试一下其他的方法。
包括你看我们的组织架构变革,也是一直在推进的。也许大家听说过我们的XO项目(2008年腾讯COO任宇昕曾推动腾讯游戏第一次组织优化,并将之命名为XO项目),我们特意给它起了一个版本号。
很多组织变革只会让大家觉得做了一轮改变,但我们有XO 1.0,XO 1.1,XO 2.0……让大家知道它会永远迭代下去。无论是游戏开发,还是公司管理,我们都相信迭代的力量。
相关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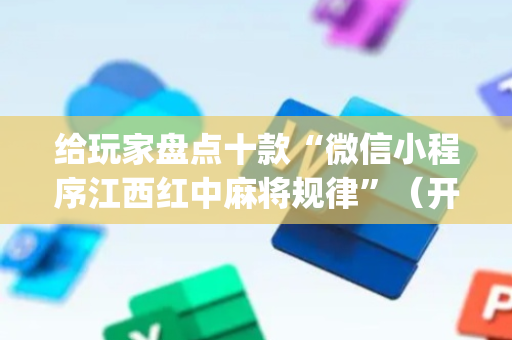
您好:这款游戏是可以开挂的,软件加微信【添加图中微信】确实是有挂的,很多玩家在这款游戏中打牌都会发现很多用户的牌特别好,总是好牌,而且好像能看到其他人...
2025-09-08 0

按照苹果的预告,9月9日,苹果就会正式发布新一代的iPhone17系列手机了。而这次,还是一共发布4款机型,分别是iPhone17、iPhone17...
2025-09-08 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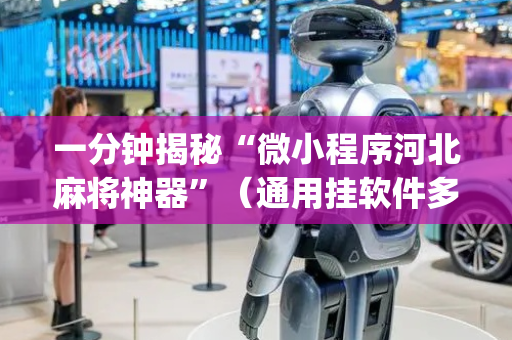
您好:这款游戏可以开挂,确实是有挂的,很多玩家在这款游戏中打牌都会发现很多用户的牌特别好,总是好牌,而且好像能看到-人的牌一样。所以很多小伙伴就怀疑这...
2025-09-08 0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