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言
自 2017 年大语言模型兴起以来,AI 技术对白领职业和知识密集型岗位的冲击,很快就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增强”(augmentation)还是 “替代”(automation),已经成为 AI 时代哈姆雷特式的问题之一。然而,尽管讨论非常热闹,但基于真实数据来研究 AI 技术应用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冲击,这样的成果却并不多见。
在 “2025 罗汉堂 - 北大国发院数字经济年会” 的现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中国公共财政研究中心主任李力行,为我们揭开了最新实证研究的一角。根据国内线上招聘网站的数据,李教授分析了不同职业、企业和城市受到 AI 技术的冲击程度,以及随之而来的劳动力市场变化。
李力行教授指出,我们可以将 AI 带来的劳动力市场冲击看作是需求与供给之间的重新匹配:需求侧存在 “直接参与 AI”、“与 AI 相关”、“非 AI 相关” 三大类型任务,供给侧也有 “与 AI 高度相关”、“与 AI 接近”、“非 AI 相关” 三大类型技能。任务与技能之间的重新匹配,将促使企业调整其生产组织和劳动力需求,也将推动劳动者提升自身技能,并能在不同的工作之间转换。

以下是李力行教授的演讲全文:
今天很高兴能代表北大国发院的研究团队来分享我们的一些研究发现。
01
基于“任务”的劳动力市场模型
我们的研究是从 “基于任务的模型”(task-based model)出发,分析 AI 技术进步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在这一视角下,企业通过组织来自不同 “职业”(occupations)的劳动者,完成生产活动。而 “职业” 则是由一系列不同的 “任务”(tasks)所组成。随着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的发展,这些任务可能被进一步拆分,使得原本被捆绑在一个职位或职业中的任务,现在可以由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地点、在不同的时间来完成。其中有一些任务可以通过技术实现自动化,而另一些任务还无法被自动化。这就是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侧。

在供给侧,同样也出现了一个拆分的过程。一名劳动者通常具备多种 “技能”(skill),因此技能原本是被捆绑在一起提供的。而现在,这些技能也可以被拆分,单独提供给市场。我们称之为从 “捆绑”(bundling)到 “解绑”(unbundling)的转变。
这样,劳动力市场上的需求和供给之间的匹配,已经不再发生在传统意义上的 “劳动”(labor)或 “职位”(jobs)层面,而是越来越发生在 “任务” 和 “技能” 的层面。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企业需要调整对生产的组织和对劳动力的需求。与此同时,劳动者个人也需要提升自身技能,在不同的任务之间转换。
现有的实证研究也对此提供了一些证据。有研究发现,美国的各行各业中,“AI 暴露度”(exposure to AI,注:一项任务的 AI 暴露度越高,则它越容易由 AI 自动完成)均值越高的行业,其用人需求正在下降。也就是说,越是容易被 AI 自动化的任务,已经越不需要人了。但与此同时,在行业内部,各类任务的 “AI 暴露度” 的分化程度(dispersion)却在上升,劳动者正在转移到行业中那些不容易被 AI 取代的任务上,比如护理等。
我想指出的是,AI 与过去几代的技术革命有非常大的不同。我们将各类职业的 “AI 暴露度” 与它们对前几轮技术的暴露度做了对比,发现 “AI 暴露度” 与 “自动化暴露度”(automation exposure)和 “信息化暴露度”(information exposure)都呈现出明显的负相关。也就是说,曾经容易被自动化和信息化替代的职位,现在反而不容易被 AI 替代。这意味着 AI 是一种与以往全然不同的 “通用目的技术”(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

02
研究设计
基于这类理论视角和现有研究,我们可以构建一个研究框架。首先需要理解政府的产业政策、税收政策等各项政策是如何影响技术创新的。随后,在新技术出现之后,它会逐渐被企业和个人采用。企业采纳新技术,可以重塑其组织和生产,并改变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个人通过学习新技术,可以提高自身的技能水平,或改变自己的职位角色。此外,对于那些受到新技术的负面冲击比较大的群体,还需要通过社会政策提供一定的保障,如社会保险和再培训等。这些都是值得探索的重要问题。

在研究中,我们主要依靠线上招聘平台的数据,分析 “AI 冲击”(AI shocks)对劳动力市场的各种影响。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衡量 “AI 冲击”。在职业层面,我们实际衡量的是不同职业的 “AI 暴露度”,也就是一个职业所涉及的各种任务由 AI 自动完成的可能性有多大。在企业层面,我们通过观察一家企业最早发布 AI 职位招聘需求的时间点,来衡量其对 AI 的暴露程度。在城市层面,我们的衡量对象包括政府的产业政策,以及 AI 职位招聘需求所占的比例。这些是我们关注的自变量。
在因变量或结果方面,我们衡量的指标包括:企业的用人需求、技能要求、绩效表现、创新成果,以及宏观层面的职业和产业结构。这些数据基本上都来自于在线招聘平台上发布的广告(posts),如:一类职业下的所有新增职位数量、招聘广告中提到的技能要求、学历要求和薪资水平等。如果我们将这些招聘平台的数据与企业层面的数据相匹配,还可以进一步分析企业的创新成果、绩效表现和人力需求等指标。在城市层面,我们将这些数据进一步整合,从而可以对职业和行业多样性等问题做出新的观察。需要说明的是,我们目前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对变量之间相关性的分析,还谈不上因果联系。
03
研究发现
我们的第一项成果是构建职业层面的 “AI 暴露度”。数据来自 “智联招聘网”(zhaopin.com):我们从 2018 年到 2024 年的招聘广告中,随机抽取了 125 万条。然后,我们对这广告所涉及的工作任务进行了识别。具体参考依据是美国 O*NET 数据库中对于工作内容描述的拆分和聚类指标,总共包括约 2 万项 “任务”,以及由此聚类而成的约 2000 种 “详细工作活动”(detailed work activities)。我们提取了招聘广告样本中对于每项工作任务的描述信息,并对任务层面的 “AI 暴露度” 做出评估。在此基础上,我们汇总形成职位层面的 “AI 暴露度”,并进一步整合为职业层面的 “AI 暴露度”。
结果显示,“AI 暴露度” 最高的 20 个职业几乎都是知识密集型的白领职业,如会计、编辑、销售、编程、审计、网页开发、电话销售等;而 “AI 暴露度” 最低的职业则大部分是体力劳动,比如洗碗工、厨师、货车司机、保洁员、搬运工、保姆等。

第二项发现是 “AI 暴露度” 的发展趋势。与其他研究类似,我们发现新发布职位的 “AI 暴露度” 正在逐渐下降。也就是说,“AI 暴露度” 较高的职位已经逐渐被机器取代了,所以企业的招聘需求开始更多地转向 “AI 暴露度” 较低的职位。

在这一点上,我们与美国的研究结果形成鲜明对比:在中国,“AI 暴露度” 最高的职位在减少;在美国,这些职位的数量却在增加。对此,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在美国,那些对 AI 暴露程度较高的职位中,也包含了大量直接参与 AI 研发和创新的职位,而这些职位的数量正在快速增长。但对于中国和其他处于技术追赶阶段的国家来说,直接投入到技术创新前沿的职位并没有那么热门,“AI 暴露度” 高的职位更多还是在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密集型白领职业。

第三项发现来自于职业的 “AI 暴露度” 与其新增职位数量之间的关联。我们发现,一个职业的 “AI 暴露度” 越高,则其新发布的职位数量越少。也就是说,相比其他职业,会计、审计、程序员等职业的新增职位数量正在减少。同时我们也观察到,“AI 暴露度” 较高的职业,往往薪资增长较慢,薪资差距较大,对学历和经验的要求也更高。这些职业的劳动者尤其面对需要提升技能的挑战。另外,在城市层面,那些对高 “AI 暴露度” 职位需求较大的城市(即 “AI 暴露度” 较高的城市),正在出现劳动力需求的总体下滑。这意味着,如果一个城市以知识密集型的白领职业为主、但并不直接从事新技术的研发,那么它在 AI 冲击下面临的风险会较高。
我们的第四项研究成果是对供给侧的衡量。这部分的数据来自国内的另一家主流招聘平台 ——“前程无忧”(51job.com)。我们尝试了多种方法,最终采用的是 “关键词提取”(keyword extraction)。我们将 “技能” 划分为 18 类:(下图中)黑色的类别是 AI 技能,被大约 4% 的招聘广告提到;蓝色的类别是那些与 AI 技能最远、相关性最低的技能,比如社交技能、工作态度和个人特质等;橙色的类别则是与 AI 技能较为接近的技能,如技术支持、数据分析、专业软件技能等。

从我们的数据来看,招聘广告中提及 AI 相关技能的比例正在增加,发布 AI 相关技能需求的用人单位占比也同样上涨,特别是在 2017 年国务院出台《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以来。
第五项发现是关于地方政府的政策。中国的地方政府在众多领域展开竞争,在前沿技术领域也不例外。我们注意到,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在其年度工作报告中都提到对 AI 产业的支持政策,尤其强调政府在协调产学研结合中的作用。通过 “事件研究法”(event study,注:研究特定事件对公司价值影响的方法),我们发现在这些政策出台之后,AI 相关的专利申请数量会出现显著增长,对 AI 技能的需求也会显著上涨,这些都体现了 AI 创新活跃度的提升。

不过,如果我们进一步将技能区分为 “与 AI 紧密相关型技能” 和 “非 AI 相关型技能”,就会发现一个令人意外的结果:需求增长更明显的反而是后者,而前者在政策出台后并未出现显著上升。我猜测这可能反映了这两类技能之间存在 “互补性”(complementary)和 “两极化”(polarization)。试想,一名 AI 工程师可能需要雇佣一位保姆来打理家务 —— 两者在技能上差异很大,但在生活中却构成互补。这一结果也呼应了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个发现,即 “AI 暴露度” 在不同任务之间的分化程度在上升,劳动者正在越来越投入到更不容易被 AI 取代的任务中。换句话说,当劳动者原本从事的任务被 AI 替代后,他们可能会转向那些更需要人际沟通等非 AI 相关技能的任务,这是潜在的转型方向之一。

另外,我们还就 AI 采用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进行了初步分析。具体的做法是将样本中的上市公司,与其所在城市中 AI 相关招聘广告的占比,进行匹配,从而衡量出企业层面的 “AI 暴露度”。结果发现,企业的 “AI 暴露度” 与其销售额、人数和全要素生产率(TFP)都存在正相关。当然,目前我们只考察了样本中的上市公司,也仅限于 AI 应用的直接效应。
最后,在城市层面,我们关注 AI 对产业结构和职业结构的影响,特别是产业和职业的多样化。结果比较意外:AI 技术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产业和职业的集中化,并导致其他产业和职业的萎缩,从而导致城市层面的产业和职业多样性出现了下降。但这仍属于初步观察。

简要小结一下:
我们基于线上招聘数据衡量了 AI 的暴露程度和采用程度。在劳动力市场中,需求侧的主要衡量点是 “任务”,供给侧的衡量点是 “技能”。由此,我们在职业、企业和城市三个层面上,考察了 AI 对劳动力需求引起的变化。我们的研究发现主要集中在职位构成和技能要求的变化上。这为我们更好地讨论 AI 究竟是 “替代还是增强” 了人的工作,提供了一些参考。
谢谢大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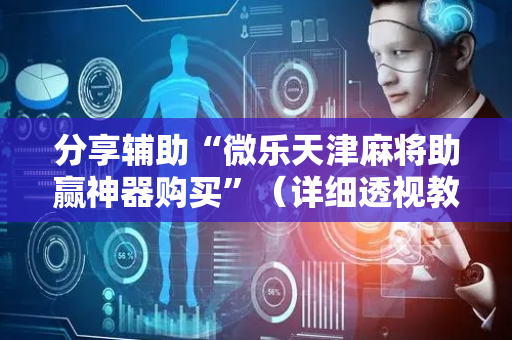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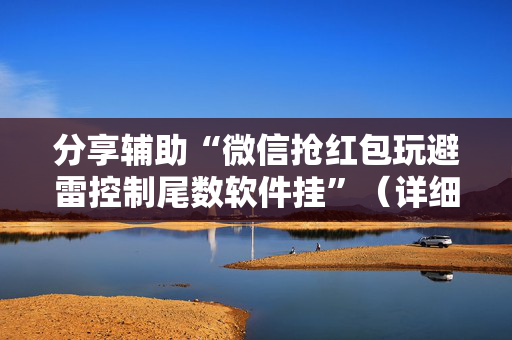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