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界2025年8月16日消息,国家知识产权局信息显示,北京字跳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申请一项名为“用于生成测试文本的方法、装置、设备、介质和程序产品”的专...
2025-08-16 0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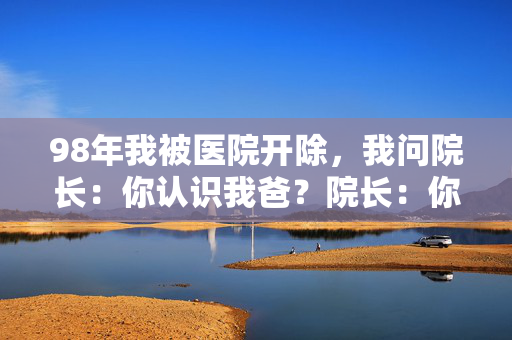
那间办公室的空气,是凝固的。
像一块放了太久的琥珀,把午后三点的阳光、浮在光柱里的尘埃,还有我,都牢牢地封在了里面。
空气里有股特别的味道。不是医院走廊里那种来苏水混合着病人忧虑的复杂气味,而是一种更沉闷的、属于旧物的味道。是红木办公桌散发的陈年木脂香,混着他保温杯里泡了半天的浓茶水汽,还有一点点,从窗台那盆半死不活的文竹根部飘上来的、泥土的微腥。
院长就坐在那张宽大的红木桌子后面。
他没有看我,视线一直落在桌上一份摊开的文件上。那是一份人事档案,我的。右上角贴着一张一寸的免冠照,照片里的我,穿着崭新的白大褂,嘴角微微上扬,眼神里是一种未经打磨的、理所当然的光亮。
现在想来,那光亮,有点刺眼。
他终于抬起头,视线越过老花镜的上缘,落在我身上。他的眼睛很平静,像两口深不见底的古井,把所有情绪都沉在了底下。
「事情的经过,我都了解了。」
他的声音和他的人一样,没什么起伏,平铺直叙,像用尺子量着说话。
「刘主任的报告,还有几位护士的说明,都写得很清楚。」
他指了指桌角另一叠纸。那几张纸的边缘有些卷曲,像是被人用力攥过。
我没说话,只是站着。双脚踩在冰凉的水磨石地面上,能感觉到一股寒意顺着脚底板,一点点往上爬,缠绕住我的脚踝,小腿,最后在膝盖窝里打了个旋。
我身上还穿着那件白大褂,口袋里插着一支英雄牌钢笔,是我爸在我入职那天送的。笔杆光滑,带着体温,此刻却像一块冰,硌着我的胸口。
「在手术室里,跟主刀医生发生争执。擅自更改用药方案。术后拒绝与患者家属沟通。」
他一字一顿地念着,像是在宣读一份判决书。每念一条,办公室里那座老式摆钟的「滴答」声,就好像更响亮一分。
滴答,滴答。
时间在被一秒一秒地切割,我的未来,似乎也在被一寸一寸地剥离。
我张了张嘴,喉咙里像是塞了一团棉花,又干又涩。
「不是那样的。」
声音小得我自己都觉得意外。
「刘主任他……他当时判断有误,那个病人的心率已经很不稳定了,再用常规剂量的肾上腺素,风险太高。我只是建议……」
「建议?」
他打断我,身体微微前倾。那副老花镜因为这个动作,往下滑了一点,搭在鼻梁上。
「你的身份,是实习医生。你的职责,是观察,是学习,是协助。不是‘建议’,更不是‘决策’。」
他的手指在我的档案上轻轻敲了敲,发出「笃笃」两声。
「年轻人有想法,是好事。但医院,首先讲的是规矩。人命关天的地方,容不得半点想当然的‘天才’。」
「天才」两个字,他咬得特别轻,却像一根针,精准地扎进了我最敏感的神经。
从医学院到这家省里最好的三甲医院,我一直是被当成「天才」来看待的。理论考试永远第一,临床操作拿满分,老师们提到我,总是一脸的欣赏。
我习惯了这种欣赏,甚至觉得那是应得的。
可现在,这两个字从他嘴里说出来,带着一种不动声色的嘲弄。
我感觉脸颊在发烫,一股热流从脖子根涌上来,直冲头顶。办公室里那股沉闷的木头和茶叶味,瞬间变得让人窒息。
「所以,」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在微微发抖,「医院的决定是?」
他把我的档案合上,动作很慢,像是在完成一个庄重的仪式。
「解除实习协议。明天你不用来了。」
一句话,轻飘飘的,却像一块巨石,轰然砸进我心里那片平静的湖。
湖水瞬间被搅得天翻地覆。
我愣住了,脑子里一片空白。那座老式摆钟的滴答声,仿佛也停了。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只剩下我急促的心跳,咚,咚,咚,撞击着耳膜。
解除实习协议?
开除?
这个词像个笑话,在我脑子里盘旋。我,被开除了?怎么可能。从我记事起,我的人生轨迹就是被设定好的。进最好的学校,读最好的专业,然后进入这家我父亲工作了一辈子的医院,成为一名出色的外科医生。
一切都该是顺理成章的。
我爸是这家医院的老人了,虽然只是后勤科的一个副科长,但几十年的人脉,谁见了他不叫一声「老哥」?刘主任见了我爸,也要客客气气地递上一根烟。
院长……院长或许不认识我爸,但他总该知道有这么一号人。
一个念头,像一根救命稻草,突然从混乱的思绪里冒了出来。
我深吸一口气,那股混杂着木香和茶气的味道,呛得我差点咳嗽出来。我强压下去,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镇定一些。
「院长,」我抬起头,直视着他的眼睛,「您……认识我爸吗?他在后勤科。」
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心里其实是带着一丝底气的。那是一种长久以来,被家庭的羽翼庇护所形成的、不自觉的底气。
我以为,他至少会愣一下,会问一句「你父亲是哪位?」,然后事情就会出现转机。
然而,没有。
院长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那两口古井依旧深不见底。
他只是平静地看着我,看了足足有五秒钟。那五秒钟,漫长得像一个世纪。办公室里的空气仿佛又重新开始流动,带着一股冰冷的压力,向我挤压过来。
然后,他开口了。
声音不大,甚至比刚才还要平淡几分。
「你爸?」
他顿了顿,嘴角似乎牵动了一下,但又不像是在笑。
「算哪根葱。」
2
「算、哪、根、葱。」
四个字。
每一个字,都像一颗小石子,被他慢悠悠地、精准地弹在我的额头上。
不疼。
但是,那种回响,却在我的颅腔里嗡嗡作响,久久不散。
办公室里的摆钟,又开始「滴答」作响了。
阳光透过窗户,斜斜地照进来,在那张红木办公桌上投下一片明亮的光斑。光斑里,几粒尘埃在舞蹈,忽上忽下,像一群迷路的精灵。
我看着那些尘埃,脑子里好像也塞满了这些东西,乱糟糟的,抓不住任何头绪。
我爸,算哪根葱?
这句话像一个巨大的问号,悬在我的头顶。
从小到大,父亲在我心里,是一棵可以遮风挡雨的大树。他不算高大,背也有些微驼,但他总能解决所有问题。
小时候,我的自行车链子掉了,满手油污也装不回去,急得直哭。他下班回来,不声不响地蹲下,三两下就弄好了,还用一块破布把链条擦得锃亮。
上学时,我和同学打架,被老师叫了家长。我以为回家免不了一顿打,可他只是听老师说完,然后平静地对我说:「男子汉,要么别动手,动手了就得认。去,给同学道个歉。」
他从没对我大声说过话,也从没炫耀过自己的「本事」。但在我的世界里,他的存在,就是一种无形的保障。
医院里的叔叔阿姨,见到我总会笑着说:「哟,老李家的公子,真是一表人才,跟你爸年轻时一个样。」
这种话听多了,就好像在我心里铺了一层厚厚的、温暖的棉花。我躺在上面,安稳又踏实。我从没想过,这层棉花,有一天会被人毫不留情地扯掉,露出下面冰冷坚硬的现实。
院长说完那句话,就重新低下了头,拿起了桌上的另一份文件,仿佛刚才那句石破天惊的话,不过是随口点评了一下今天的天气。
他没再说「你可以走了」,但他整个人的姿态,都在告诉我:这场谈话已经结束了。
我站在原地,手脚冰凉。
那件崭新的白大褂,此刻像一件租来的戏服,穿在身上又沉又滑稽。口袋里的那支英雄钢笔,也失去了温度。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那间办公室的。
记忆像一部跳帧的黑白电影。
画面一转,我已经站在了医院大门口。
正是下班高峰期,人来人往。穿着白大褂的医生护士,推着轮椅的家属,还有那些脸上写满焦虑和期盼的病人,像潮水一样从我身边涌过。
空气中,那股熟悉的来苏水味道,此刻闻起来却无比陌生。
我脱下白大褂,胡乱地团成一团,塞进我的帆布挎包里。
白大褂一脱,我好像瞬间就从这个世界里被剥离了出去。我不再是「李医生」,不再是这家医院的一份子。我只是一个穿着灰色T恤的普通年轻人,站在街边,茫然四顾。
夕阳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投在人行道上,被来来往往的脚踩得支离破碎。
我该去哪儿?
回家吗?
怎么跟我爸妈说?
说我被开除了?说院长说我爸「算哪根葱」?
我无法想象父亲听到这句话时的表情。他会是怎样的感受?是愤怒,是难堪,还是……无奈?
我沿着马路,漫无目的地走着。
街道两旁的梧桐树,叶子已经开始泛黄。风一吹,就有几片叶子打着旋儿落下来,悄无声息地躺在地上。
九八年的城市,还没有那么多高楼大厦。马路上跑的,大多是二八大杠的自行车,偶尔有几辆红色的夏利出租车开过,留下一串尾气。
路边的小卖部里,老板正搬着一箱健力宝出来。几个放学的孩子围着冰柜,在争论是买五毛钱一根的绿豆冰棒,还是八毛钱一根的娃娃头。
这一切,都和我无关了。
我的世界,在今天下午三点,被按下了暂停键。
我走到一个街心公园,找了条长椅坐下。
公园里有几个老头在下象棋,楚河汉界,杀得正酣。一个老太太推着婴儿车,在旁边慢慢地踱步。不远处,几个年轻人正在打篮球,球鞋摩擦地面的声音,篮球撞击篮板的声音,还有他们的呼喊声,混杂在一起,充满了生命力。
我从挎包里掏出那件被我揉得皱巴巴的白大褂。
我把它展开,铺在膝盖上。
衣服很新,领口和袖口都还带着浆洗过的硬挺。左胸的口袋上,用蓝色的线,工工整整地绣着我的名字,还有一个编号。
我盯着那个名字,看了很久很久。
我一直以为,我穿上这件衣服,是天经地义的。就像鱼儿天生就该在水里游,鸟儿天生就该在天上飞。
现在我才发现,我错了。
我从来不是什么天生的医生。我只是一个幸运地走在被铺好的路上的孩子。而现在,路,断了。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公园里的路灯一盏盏亮起,昏黄的光晕,把周围的一切都染上了一层不真实的色彩。
蚊子开始多了起来,在耳边嗡嗡地叫。
我把白大褂重新叠好,放回包里。然后我站起身,拍了拍裤子上的灰。
我还是得回家。
无论如何,我得回去,面对这一切。
3
推开家门的时候,晚饭的香气正从厨房里飘出来。
是红烧肉的味道,我妈的拿手菜。肥瘦相间的五花肉,用冰糖和老抽熬得色泽红亮,香气霸道,能钻进每一个晚归人的鼻孔里。
「回来啦?」
我妈系着围裙,从厨房里探出头来,脸上带着笑。她的头发上沾了一点白色的面粉,应该是刚才在和面。
「今天怎么这么晚?饿了吧?马上就好,再炒个青菜就行。」
我爸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正戴着老花镜看晚报。听到我回来的声音,他把报纸往下挪了挪,露出眼睛。
「嗯。」
我含糊地应了一声,换了鞋,把挎包放在玄关的柜子上。我不敢看他们的眼睛。
客厅的灯光是暖黄色的,照在人身上,很温暖。可我却觉得浑身发冷。
「快去洗手,准备吃饭。」我爸说,然后又把报纸举了起来,挡住了他的脸。
我走进卫生间,打开水龙头。
冰凉的水流冲刷着我的手,也好像在试图冲刷掉我心里的那份灼热和慌乱。
镜子里的人,是我,又不是我。
脸色苍白,眼神涣散,嘴角紧紧地抿着。那不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该有的样子。
我用冷水泼了泼脸,抬起头,水珠顺着我的脸颊滑落,滴在洗手池里,发出「嗒、嗒」的轻响。
我对着镜子,反复练习着一个听起来自然的微笑。
可无论怎么扯动嘴角,那个笑容都比哭还难看。
饭桌上,我妈不停地往我碗里夹肉。
「多吃点,看你最近都瘦了。实习很辛苦吧?」
「还行。」我埋着头,拼命地往嘴里扒饭。食物的味道,我一点也尝不出来。嘴里像塞满了木屑,难以下咽。
「今天你们刘主任还碰到我了,」我爸放下筷子,喝了一口杯子里的白酒,慢悠悠地说,「他还夸你来着,说你脑子活,学东西快。就是……」
他顿了一下。
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
「就是性子有点急,让我跟你说说,在科室里要多听多看,别着急发表意见。年轻人嘛,稳重一点总没错。」
我爸的语气很平淡,就像在说一件很平常的事。
我却觉得,每一个字,都像一记耳光,扇在我的脸上。
原来,刘主任早就给我爸打过「预防针」了。
而我,还傻乎乎地以为,他是欣赏我的。
我扒饭的动作停了下来,嘴里的饭菜,再也咽不下去了。
「怎么不吃了?」我妈关切地问。
「……吃饱了。」
我放下碗筷,站起身,「我有点累,先回房间了。」
我几乎是逃也似的,回到了自己的卧室,关上了门。
我靠在门板上,背心一片冰凉。
客厅里,隐约传来我爸妈的对话声。
「这孩子今天怎么了?是不是在医院受委屈了?」是我妈的声音。
「年轻人,工作上有点不顺心,正常。让他自己静一静吧。」是我爸的声音。
他还不知道。
他还以为,我只是「工作上有点不顺心」。
我的房间很小,一张床,一个衣柜,一张书桌。书桌上,堆满了各种医学书籍。《系统解剖学》、《外科学总论》、《诊断学》……每一本,我都翻了无数遍,书页的边缘都起了毛。
我曾经以为,这些书,就是我的整个世界。
现在,这个世界,崩塌了。
我在书桌前坐下,拉开抽屉。
抽屉里,放着一个相框。
照片是去年夏天拍的,在我拿到医院实习通知书那天。照片里,我穿着白大T恤,笑得一脸灿烂。我爸搭着我的肩膀,他也笑着,眼角的皱纹里,都藏着笑意。背景,就是我们医院那栋标志性的门诊大楼。
那时候,我们都以为,未来就像照片里的天气一样,晴空万里。
我把相框倒扣在桌面上,再也不想看到那张笑脸。
那一晚,我失眠了。
我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一遍遍地回放着下午在院长办公室里的情景。
院长的眼神,他的语气,还有那句「算哪根葱」。
每一个细节,都清晰得如同刀刻。
天快亮的时候,我才迷迷糊糊地睡着。
我做了一个梦。
梦里,我又回到了那间办公室。院长还是坐在那张红木桌子后面,平静地看着我。
他问我:「你的路,在哪里?」
我张着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然后,整个办公室开始融化,像被火烤的蜡烛。红木桌子,文件,那盆文竹,都变成了流动的液体,把我包裹起来,往下拖拽。
我拼命挣扎,却越陷越深。
就在我快要窒息的时候,我醒了。
一身冷汗。
窗外,天已经大亮。新的一天,开始了。
而我,却成了一个无所事事的人。
我躺在床上,听着客厅里传来我爸妈准备上班的声响。开门声,关门声,然后是楼道里渐渐远去的脚步声。
家里,又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我该怎么办?
这个问题,像一块巨石,压在我的胸口。
我不能再这样瞒下去了。
我深吸一口气,从床上坐起来。
是时候,面对现实了。
4
我是在晚饭的时候,把一切都说出来的。
那天,我妈特意包了饺子,猪肉白菜馅的,我最喜欢的口味。
饭桌上,气氛有些沉闷。我一整天都没出房门,我爸妈大概也察觉到了不对劲。
我爸给我倒了一杯酒,很小的杯子,是那种喝白酒用的二两杯。
「有心事,就说出来。别憋在心里。」他说。
我看着杯子里清澈的液体,闻着那股辛辣的酒气,终于鼓起了勇气。
「爸,妈。」
我开口,声音有些沙哑。
「我……被医院开除了。」
话一出口,整个世界都安静了。
我妈夹饺子的筷子,停在了半空中。
我爸端着酒杯的手,也僵住了。
时间,仿佛又回到了院长办公室里的那一刻,凝固了。
过了好几秒,我妈才反应过来,她的筷子「啪嗒」一声,掉在了桌子上。
「开……开除?你说什么胡话呢?」她的声音在发颤。
我不敢看她的眼睛,只能低着头,盯着自己面前那碗饺子。热气氤氲,模糊了我的视线。
我把昨天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全都说了出来。从手术室里的争执,到院长办公室里的谈话。
说到最后那句「你爸算哪根葱」时,我停住了。
我实在说不出口。
那句话,像一根鱼刺,卡在我的喉咙里,吐不出,也咽不下。
我爸一直沉默着,一句话也没说。
等我说完,他才慢慢地把手里的酒杯放下,发出「嗒」的一声轻响。
然后,他站起身,走到阳台,点了一根烟。
他很少在家里抽烟,除非是真的遇到了什么烦心事。
我妈的眼圈红了,她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却又不知道该从何说起。最后,只化成了一声叹息。
「先吃饭吧,饺子要凉了。」
那一顿饭,我们三个人,谁都没有再说话。
只有咀嚼的声音,和窗外偶尔传来的汽车鸣笛声。
吃完饭,我妈默默地收拾着碗筷。我爸还在阳台上抽烟,他的背影,在昏黄的灯光下,显得有些萧条。
我走过去,站在他身后。
「爸。」
他转过身,把烟头在栏杆上摁灭。
「那个院长,姓王,对吧?」他问。
我点了点头。
「我知道他。」我爸的声音很平静,「他不是我们医院提拔上去的,是上面直接空降下来的。刚来不到半年。」
「他……」
「他是个有本事,也有脾气的人。眼里不揉沙子。」我爸打断了我的话。
他看着我,眼神很复杂。有失望,有心疼,但没有责备。
「你觉得,你被开除,是因为你顶撞了刘主任,还是因为……别的?」
我愣住了。
我一直以为,我被开除,就是因为那场手术室里的风波。
可现在听我爸这么一问,我忽然觉得,事情可能没有那么简单。
「你的毕业论文,写的是什么?」我爸又问。
「关于……微创手术中,一种新的缝合技术。」
「那篇论文,是不是参考了很多国外的资料?还提出了一些,跟现在主流观点不太一样的看法?」
我点了点头,心里越来越困惑。我爸是后勤科的,他怎么会知道这些?
「你那篇论文,我找人看过。」我爸叹了口气,「写得很好,很有想法。但是,太超前了。」
「超前?」
「对,超前。」我爸说,「你提出的那些技术和观点,在国内,根本没有几家医院有条件实现。你等于是,写了一份屠龙之术。屠龙之术,是用来扬名立万的,不是用来在一家讲究论资排辈、按部就班的医院里,安身立命的。」
我呆呆地听着,感觉自己像个傻子。
我一直引以为傲的才华,我那些自以为是的「想法」,在现实面前,原来是这么的不堪一击。
「刘主任他们,不喜欢你这样的‘天才’。因为你的存在,会让他们觉得自己落伍了,无能了。所以,他们会想尽办法,把你排挤出去。」
「那……王院长呢?」我忍不住问,「他也不懂吗?」
「他懂。他太懂了。」我爸的嘴角,泛起一丝苦笑,「正因为他懂,所以他才更不能留你。」
「为什么?」
「因为他刚来,根基不稳。他需要团结大多数人,而不是为了一个还没毕业的实习生,去得罪整个外科的元老。更何况,这个实习生,还那么不知天高地厚,锋芒毕露。」
我爸的话,像一把手术刀,精准地剖开了我一直不愿面对的现实。
原来,我不是输给了某个具体的人,而是输给了这个环境,输给了那些看不见的规则。
最可笑的是,我还天真地以为,搬出我爸,就能解决问题。
夜色深了。
我和我爸在阳台上站了很久。
风吹过来,带着一丝凉意。
「爸,」我低声说,「对不起。」
「傻孩子,说什么对不起。」我爸拍了拍我的肩膀,「路还长着呢。摔一跤,不是坏事。至少让你知道了,这世上,不是所有路都是平的。」
他顿了顿,又说:「明天,我去找找老同学,看看别的医院有没有机会。」
我摇了摇头。
「不用了,爸。」
那一刻,我心里突然有了一个决定。
「我想……换条路走走。」
5
接下来的一个月,我把自己关在家里,哪儿也没去。
我爸妈以为我还在为被开除的事情难过,也没怎么打扰我,只是每天变着花样地给我做好吃的。
其实,我不是在消沉。
我是在思考。
那晚和我爸在阳台上的谈话,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脑子里的另一扇门。
我第一次开始审视自己,审视我过去二十年的人生。
我发现,我一直活在一个巨大的、温暖的泡沫里。这个泡沫,是我的家庭,我的学校,我那些顺风顺水的经历,共同吹起来的。
在泡沫里,我看到的,都是彩色的,美好的。
现在,泡沫破了。
我看到了泡沫外面,那个真实、粗粝,甚至有些残酷的世界。
我需要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
我把我那些医学书,一本一本地,重新整理好,放进了箱子里。
然后,我走出了家门。
我没有去找工作。我开始在城市里游荡。
我去了人才市场。那里人山人海,每个人脸上都写着迷茫和焦虑。我看到一个跟我年纪相仿的年轻人,因为一份月薪八百块的文员工作,跟人争得面红耳赤。
我去了火车站。广场上,坐满了扛着大包小包的农民工。他们的脸,被太阳晒得黝黑,手上布满了老茧。他们在等一趟不知道开往何方的绿皮火车,眼神里,有对未来的期盼,也有对未知的惶恐。
我去了城郊的一个菜市场。凌晨四点,天还没亮,那里已经灯火通明。菜贩们忙着卸货,摆摊,吆喝。空气中,弥漫着泥土、蔬菜和鱼腥的混合气味。那种味道,充满了最原始的、最鲜活的生命力。
我看到一个卖豆腐的阿姨,她的手,常年泡在水里,又白又肿。可她跟客人说笑的时候,眼睛里是有光的。
我开始明白,我爸说的那句话。
「这世上,不是所有路都是平的。」
也开始明白,王院长那句「算哪根葱」,或许,并不仅仅是一句轻蔑的斥责。
它更像一个问题。
一个,需要我自己去回答的问题。
我,李XX,脱掉了那身白大褂,放下了那些书本知识,我到底是谁?我能做什么?我算什么?
一个月后,我对我爸妈说,我想去南方。
去那个据说遍地是机会,也遍地是挑战的地方。
我妈哭了。她舍不得我。
我爸沉默了很久,最后只说了一句:「想好了,就去吧。家里不用你惦记。」
临走前一天晚上,我爸把我叫到书房。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递给我。
信封很厚,很沉。
「这里是五千块钱。省着点花。」他说,「到了那边,别急着找工作。先安顿下来,多走走,多看看。记住,做人,比做学问更重要。」
我接过信封,眼眶有点热。
那个年代,五千块钱,是我爸妈将近一年的工资。
「爸,」我声音哽咽,「那句话……院长说的那句话……」
我还是没能说出口。
我爸却好像知道我要说什么。
他笑了笑,那笑容里,没有我担心的难堪和愤怒,只有一种释然。
「那句话,他说得没错。」
我愣住了。
「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后勤科长,每天跟柴米油盐、灯泡水管打交道。我这一辈子,没做过什么大事,也没什么能耐。」
他看着我,目光温和而坚定。
「但是,我把你养大了。我教会了你怎么走路,怎么拿筷子,怎么堂堂正正地做人。我觉得,这就够了。」
「孩子,」他拍了拍我的手,「一个人,是不是一根‘葱’,不是别人说了算的。是你自己,用你做的事,走的路,活出来的。」
那一刻,我心里那根卡了很久的鱼刺,好像,终于被拔了出来。
6
我坐上了南下的绿皮火车。
火车哐当哐当,载着我,驶向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
车厢里,挤满了人。空气中,是泡面、汗水和劣质香烟混合的味道。
我靠在窗边,看着窗外的景色飞速倒退。田野,村庄,小山坡……所有熟悉的一切,都在离我远去。
我心里,没有害怕,反而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和期待。
我到了深圳。
九八年的深圳,像一个巨大的建筑工地。到处都在盖房子,到处都是脚手架。空气中,永远飘着一股尘土的味道。
我用我爸给的钱,在一个人蛇混杂的城中村里,租了一个小小的单间。
房间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窗户外面,就是邻居家的厨房。每天都能闻到各种各样的菜香。
我开始找工作。
我没有再去人才市场,也没有投简历给那些写字楼里的公司。
我去了那家城中村里,唯一的一家社区卫生服务站。
那与其说是一个卫生站,不如说是一个大一点的药店。十几平米的地方,一半是药柜,一半是问诊台。
坐诊的,是一个姓陈的老医生。头发花白,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的眼镜。
我走进去的时候,他正在给一个小孩看病。
小孩在哭,他妈妈在一旁焦急地哄着。
陈医生不慌不忙,拿着压舌板,很耐心地检查着小孩的喉咙。他的动作很轻柔。
「没事,就是有点扁桃体发炎。」他笑着对那个妈妈说,「我给他开点药,回去多喝水,别吃上火的东西,过两天就好了。」
他开的药,都是最便宜,也最常见的那几种。
那个妈妈千恩万谢地带着孩子走了。
我走上前,对陈医生说:「您好,我叫李想,我想在您这里找份工作。」
我给自己起了个新名字。
陈医生抬起头,透过厚厚的镜片打量着我。
「学过医?」
「嗯,医学院毕业的。」
「有医师资格证吗?」
我摇了摇头。
「那你能干什么?」
「我什么都能干。」我说,「我可以帮您抓药,打扫卫生,整理病历,给病人量体温、测血压……」
陈医生看着我,沉默了一会儿。
「工钱可不高。」
「没关系。」
「管住不管吃。」
「行。」
就这样,我留了下来。
我的工作,就是打杂。
每天,我第一个到卫生站,开门,打扫卫生,把所有的东西都擦得一尘不染。
然后,我跟着陈医生,学习怎么辨认中药,怎么用戥子称量。他的手很稳,一抓一个准。
有病人来的时候,我就负责引导,倒水,量体温。
我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天才」,我成了一个服务者。
我开始学会微笑,学会耐心地倾听。
来这里看病的,大多是附近的工人和他们的家属。他们的问题,也大多是些头疼脑热、跌打损伤的小毛病。
但对他们来说,每一次生病,都是一件大事。
我记得有一个在工地上开塔吊的大哥,因为中暑被工友们抬了过来。他脸色煞白,浑身是汗。
陈医生给他刮了痧,又让他喝了一大碗藿香正气水。
我给他扇着风,听他断断续续地说,他家里有两个孩子要读书,他一天都不能歇。
我看着他那张饱经风霜的脸,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生命,是如此的脆弱,又是如此的坚韧。
在这里,我见到了形形色色的人,听到了各种各样的故事。
我的世界,不再只有手术刀和教科书。它变得具体,变得鲜活,变得充满了人间的烟火气。
我开始明白,医学的意义,并不仅仅是攻克那些疑难杂症,发表那些高深的论文。
它更在于,为每一个普通的、鲜活的生命,提供最基本的健康保障,和最温暖的人文关怀。
7
我在卫生站,一待就是两年。
这两年里,我考取了医师资格证。
陈医生开始让我独立处理一些简单的病例。
我第一次给病人开处方的时候,手都在抖。
那是一个因为搬重物而闪了腰的年轻人。我给他做了详细的检查,开了活血化瘀的膏药,又叮嘱他要注意休息。
他走的时候,对我说了一声「谢谢你啊,李医生」。
那一声「李医生」,比我过去听过的所有赞美,都更让我心安。
2000年的夏天,深圳下了一场特大暴雨。
整个城市,都泡在了水里。
我们所在的城中村,是重灾区。水淹到了一楼,停水停电。
卫生站也进了水,很多药品都被泡了。
我和陈医生,把还能用的药品,都搬到了二楼。然后,我们穿着雨衣,趟着齐腰深的水,在村子里巡诊。
很多人因为淋雨和喝了不干净的水,开始上吐下泻。
我们带的药很快就用完了。
我记得,当时有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发高烧,已经有些脱水了。
她妈妈抱着她,哭得撕心裂肺。
「医生,求求你们,救救我女儿!」
陈医生摸了摸孩子的额头,脸色凝重。
「必须马上送医院,不然会有危险。」
可是,外面的路,全都被水淹了,救护车根本进不来。
所有人都束手无策。
就在这时,我想起了我大学时学过的一种土办法——物理降温,配合穴位按压。
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唯一的办法。
我让孩子妈妈找来白酒和毛巾,然后,我开始用最原始的方法,为孩子擦拭身体,降温。同时,用我并不算熟练的手法,按压她的合谷、曲池等穴位。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所有人都围着我们,大气都不敢出。
我满头大汗,手臂酸痛,但我的手,一直没有停。
不知道过了多久,孩子身上的热度,终于开始慢慢退去。她的呼吸,也平稳了下来。
孩子妈妈「扑通」一声,跪在了我面前。
我赶紧把她扶起来。
那一刻,我看着她脸上纵横的泪水,看着周围人如释重负的表情,我心里,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满足感。
我不需要先进的仪器,不需要高深的理论。
我用我的双手,我的知识,挽救了一个小生命。
那一刻,我终于找到了那个问题的答案。
我,李想,是一个医生。
一个,能为普通人解除病痛的,普普通通的医生。
这就够了。
8
暴雨过后,城市很快恢复了正常。
卫生站也重新开张了。
村子里的人,都对我客气了很多。他们见到我,都会笑着喊我一声「李医生」。
有一天,陈医生把我叫到一边。
「小李啊,」他说,「你是个有本事的人,不该一直窝在我这个小地方。」
「陈医生,我……」
「你听我说完。」他摆了摆手,「前几天,市里人民医院的王院长来我们这里视察灾情,我跟他提了你。」
我心里「咯噔」一下。
姓王?
不会那么巧吧?
「他看了你的档案,对你很感兴趣。他说,他们医院新成立了一个微创外科中心,正缺人手。他想让你过去试试。」
我愣住了,半天说不出话来。
命运,真是个奇妙的东西。它关上一扇门,又会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为你打开一扇窗。
几天后,我接到了市人民医院的面试通知。
面试我的,正是王院长。
他比两年前,看上去老了一些,头发也白了不少。
他还是坐在那张熟悉的红木办公桌后面,办公室里,还是那股熟悉的、木头和茶叶混合的味道。
只是,这一次,我的心,很平静。
他看着我的简历,看了很久。
「这两年,都在社区卫生站?」他问。
「是的。」
「为什么?」
我想了想,说:「因为在那里,我找到了当医生的感觉。」
他抬起头,那双古井般的眼睛,第一次,有了一丝波澜。
「哦?说说看。」
我把我这两年的经历,我的所见所闻,我的所思所想,都平静地告诉了他。
我没有抱怨,也没有煽情。
我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
我说完了,他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笑了。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笑。
「很好。」他说,「你明天,就来上班吧。」
我走出了那间办公室。
阳光正好,透过走廊的窗户,照在我身上,暖洋洋的。
我没有回头。
但我知道,这一次,我脚下的路,是我自己,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它或许不平坦,但它,通向我想要去的未来。
后来,我才知道。
当年,王院长之所以对我说那句话,不仅仅是因为要平息科室的矛盾。
更是因为,他从我的档案和论文里,看到了他自己年轻时的影子。
他也是一个「天才」,也曾因为锋芒毕露,而被下放到了偏远的乡镇卫生院,一待就是十年。
那句「算哪根葱」,是他当年,对自己说过无数遍的话。
他是在问我,也是在问他自己。
一个人,真正的价值,到底是什么?
现在,我想,我已经有了我的答案。
相关文章

金融界2025年8月16日消息,国家知识产权局信息显示,北京字跳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申请一项名为“用于生成测试文本的方法、装置、设备、介质和程序产品”的专...
2025-08-16 0

金融界2025年8月16日消息,国家知识产权局信息显示,苏州哥地光子技术有限公司取得一项名为“一种可调式多功能加热炉”的专利,授权公告号CN22322...
2025-08-16 0

现在人们打棋牌麻将谁不想赢?手机微乐麻将必赢神器但是手机棋牌麻将是这么好赢的吗?在手机上打棋牌麻将想赢,不仅需要运气,也需要技巧。掌握的棋牌麻将技巧就...
2025-08-16 0

PC 塑料,即聚碳酸酯,凭借出色的耐冲击性、透明度及耐热性,在电子电器、汽车制造、医疗器械等领域大显身手。然而,其性能优劣与成分紧密相关,这就凸显了成...
2025-08-16 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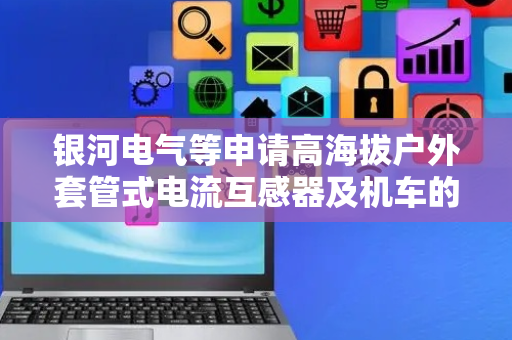
金融界2025年8月16日消息,国家知识产权局信息显示,银河电气科技有限公司;江苏伟正电气科技有限公司申请一项名为“高海拔户外套管式电流互感器及机车的...
2025-08-16 0

金融界2025年8月16日消息,国家知识产权局信息显示,苏州瑞比机电科技有限公司申请一项名为“一种手动瓷砖切割机”的专利,公开号CN120481081...
2025-08-16 0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