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之家 7 月 12 日消息,科技媒体 Gsmarena 昨日(7 月 11 日)发布博文,分享了关于三星 Galaxy S25 FE 手机的信息,...
2025-07-12 0
非常感谢邀请我参加罗汉堂年会,在座的很多嘉宾都是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和研究人员。我的背景是计算机科学,从事人工智能的研究已经有大约 30 年了。我的 AI 之旅起点其实离这里不远,我在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获得硕士学位,之后前往卡内基梅隆大学继续攻读人工智能博士。当时 AI 还不是一个热门话题,因为那个时期技术还不够成熟。毕业之后我加入了 IBM 研究院,后来去了 Facebook ,再之后加入了阿里巴巴。
今天我的分享主要是回顾 AI 的发展历程,包括其经历的多个周期起伏。我提前做一个免责声明:这些都是我个人的观点和看法,并不代表阿里巴巴的立场。
1
人工智能发展的历史回顾
如果我们比较最近几波技术发展趋势,包括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以大语言模型为驱动的人工智能,一个很明显的趋势就是大语言模型的扩散曲线非常陡峭。从这个曲线的对比可以看到 AI 的未来潜力是无限的,我们现在只是在这一范式的起步期。从本质上来讲,AI 可以说是对人类智能活动的一种替代和升级,它将会对人类社会几千年来积累的经济、社会、组织、文化的方方面面都造成巨大的影响。这是为什么一方面整个社会都觉得很兴奋,一方面也会让人有一点恐慌,担心我们是不是做好了准备。
回顾从 1956 到 2025 年——差不多 70 年来——的 AI 历史,我们看到这个发展曲线有高潮也有低谷,经历了多个周期。简单来讲,在 1990 年以前,AI 研究主要以“知识驱动”为核心,即将人类专家知识灌入 AI 系统中。2000 年左右,随着大规模数据用于训练机器学习模型和语言模型,AI 研究进入“数据驱动”阶段。“知识驱动”和“数据驱动”这两种范式此消彼长,这是过去几十年来 AI 发展的主要特点。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这个名词最早是在 1956 年的达特茅斯会议上由 John McCarthy 等四位教授提出的。早期的 AI 研究和我们现在的研究非常类似,比如做定理证明、棋类博弈,还提出了神经网络的最早版本,也就是感知器(perceptron)。但是到 1960 年代,当时的机器翻译漏洞百出,无法满足冷战时期对英俄互译的需求,而人们设想的通用机器人也遥不可及。英国政府发布的《莱特希尔报告(Lighthill Report)》认为当时的 AI 技术只能解决无足轻重的玩具类问题,难以应对真实需求。于是 AI 迎来了第一波寒冬。
第二波 AI 热潮出现在 1970 年代末到 1980 年代。当时采用“专家系统(expert system)”的思路,把各领域人类专家的知识引入到 AI 系统中。这条路线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要解决更复杂的问题就需引入更多的人类知识,而不同人的知识会相互冲突,如何维护这样庞大的知识库就成了一个工程难题。同一时期,神经网络继续发展,计算机视觉和自然语言处理开始兴起。1990 年代初,日本提出了第五代计算机计划,开发智能计算机,然而并未取得重大突破,原因很大程度在于当时的软硬件受限,专家知识共享也遇到瓶颈,技术难以大规模落地。
从 2000 年开始,统计机器学习兴起,神经网络相对低潮。一个显著趋势是数据驱动 AI 的进步,在机器翻译、计算机视觉、人机对弈等领域,出现了 Google Translate、IBM Deep Blue 等标志性成果。这些 AI 系统在特定领域表现出色,但应用范围有限,仍缺乏泛化能力。
到了 2010 年之后——特别是从 2012 年开始——深度学习、深度神经网络再次崛起。Geoffrey Hinton 及其学生将神经网络从几层扩展到数十层,在图像识别(如斯坦福大学教授李飞飞研究组建立的图像分类数据集 ImageNet)、语音识别、自然语言机器翻译等任务中展现了优异的效果。从 2014 年起,我们见证了基于深度学习的 AI 浪潮进一步兴起,基于神经网络的技术解决了部分科学和棋类的问题,例如做蛋白质结构预测的 AlphaFold 和做围棋的 AlphaGo,后者的成功不仅是科学上的突破,更引起了广泛的公众关注。
我个人认为 2020 年基于 GPT-3 的 ChatGPT 的发布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人们能够直接与 AI 互动,有感性的认识,并惊叹于其表现。GPT-3 在技术路径上与 GPT-1、GPT-2 相似,但模型规模和数据量大幅增加,模型性能也得到显著提升。ChatGPT 发布后,全球大量用户的使用提供了丰富的用户数据和互联网语料,从而进一步增强了模型效果,大语言模型让用户感知到它具备了一定的智能能力。这标志着新的研究范式的形成:无论是在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视觉,还是其他领域,国内外纷纷涌现出类似的基础模型(foundational model)。到了基础模型阶段,大家熟悉的“数据、算法和算力”三要素依然是关键。用一句话概括的话,利用能源提供海量算力,从大规模数据中提取知识并形成智能,这是驱动目前这一整套AI的底层逻辑。
2
主要的技术发展路径
从整个技术范式来看,AI 是一个很大的集合,包括基于规则、基于统计的方法,既有机器学习也有非机器学习的方法。机器学习是用数据的方式去学习,而更进一步的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则是用多层神经网络的方法来学习。
我大概讲一下机器学习的几种主要技术,因为很多机器学习的技术仍然在继续沿用。比如,强化学习(reinforcement learning)以前是用来解决机器人前进路线的规划问题,解决游戏场景的策略问题。在游戏场景中,即时的奖励反馈非常适合于训练模型学习信号。另一类是监督学习(supervised learning):我们可以给一项任务标注一些数据,比如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然后用这些带标注的数据来训练模型。但传统监督学习依赖人工标注数据,成本会非常高,难以大规模应用。还有一类是无监督学习(unsupervised learning),包括现在的大语言模型,不需要人工标注,只要爬取大量数据后,通过数据本身去挖掘潜在的知识。
到 GPT 特别是 GPT-3 出现以后,AI 技术发展整体走向了以大语言模型为代表的基础模型。大语言模型本质上是能力非常强大的神经网络。这种范式虽然来自于深度学习,但已经大不相同了。一方面,之前的一些技术问题在大语言模型中还会存在,比如机器幻觉(hallucination)或过拟合(overfitting)的问题;另一方面,新模型大大拓展了 AI 能力的边界,具有更强的泛化能力。基础模型这个范式可以说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
这个阶段的关键技术发展有预训练(pretraining),包括具备高效并行能力的 Transformer 架构。同时,由于训练数据来源广泛,我们在处理新任务时,可以不用重新训练模型,仅提供样例(demonstration)、小样本(few-shot learning)或指令(instruction),模型就能完成任务。因此,大语言模型比以往的针对特定领域的 AI 要表现出更强的泛化能力。这也解决了传统监督学习中的痛点,不再需要大量昂贵的人力来标注数据。
但大语言模型也引发了一系列问题,比如 AI 如何与我们的项目任务、人类价值观、社会伦理和文化习俗对齐(alignment)。这就涉及到多方面的对齐技术,如监督微调(SFT)、强化微调(RFT)等,这些都是基于强化学习的技术。
从去年下半年以来,在线推断(online inference)、在线学习(online learning)和推理(reasoning)成为新的发展方向。大家希望通过构建“思维链”(chain of thought),让模型学会遇到问题能够规划解决思路,如果中途发现思路不对,还能返回来换一种思路重试。这样能够大幅提升模型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类似于人类的“慢思考”。
从底层的知识体系来看,大语言模型发展已经历了从自然语言文本中提取知识、到从图像、语音、视频等多模态中提取知识、然后到逻辑推理,再到发展成为智能体(agent)的进程。智能体能够完成更复杂的任务,而不同智能体的组合,甚至能够模拟一个小型团队执行复杂的工作流。2025 年也被很多人称为“智能体元年”,它将带来越来越多的技术影响力和商业价值。
3
阿里巴巴的大语言模型开发
训练一个大语言模型需要具备从底层到顶层的全栈能力。在这方面,云厂商具有独特的优势。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的云厂商都具备从提供底层的 AI 芯片到提供云算法平台的能力,再到提供分布式的 AI 框架和算法库以支持模型的训练和推理等,然后到模型训练完成后在云平台上进行部署,包括开源(open source)模型和闭源(closed source)模型。以阿里巴巴为例,我们一方面构建了中国的开源模型社区 ModelScope,大家可以把开源模型放上去供开发者使用下载。同时我们也部署了自己的闭源模型供客户使用。
在基础模型或大语言模型方面,阿里巴巴其实起步较早。继 2017 年 Google 提出的 Transformer 架构成为这波 AI 革命的基础之后,我们在 2018 年基于 BERT 模型开发了自己的创新模型 StructBERT,重点考虑了句子结构信息,使模型能够更好地建模语义。
从 2019 年到 2020 年,我们陆续构建了自己的预训练模型,包括参数规模从百亿、万亿甚至到十万亿级的。从 ChatGPT 发布以来,我们发现这条路线很有潜力,也意识到要进一步加大模型规模、提升训练框架的计算效率,同时对数据处理也要更加精细。在此基础上,我们发布了“千问”系列的自然语言模型、“万相”系列的文生图、文生视频模型,以及面向具体任务的下游应用模型,如代码助手、角色陪伴等。
2024 年我们推出了“百炼”平台,用户可以在平台上调用我们的模型,完成各自的下游任务。目前,“千问”模型系列不仅在中国也在全球范围内处于用户数量领先的地位,甚至在业界达到第一。
AI 应用这个领域发展过于迅速,会让人感到研究有时候跟不上产业的节奏。一个重要的方向是 AI 在软件工程方面的应用。我们注意到,预训练模型其实从 2020 年就已经在这个方向进行研究和应用了。大约在一年半前,我们开始看好这个方向并加大投入,这可能是 AI 落地进展最好的一个方向。
比如一个 AI 程序员可以完成复杂的软件开发任务。我把需求告诉 AI 程序员,它能够进行任务拆解、规划并执行。如果过程中出现问题,它可以进行验证、修正和测试,最后汇总结果。人的作用主要是在于提出需求、定义问题、确认结果,中间大多数环节都由 AI 完成。这不只是适用于软件工程,也许未来很多任务都可以由 AI 完成,人类只需负责最顶层的这三件事,其余的交给 AI 就行了。
还有一个方向是我们如何利用 AI 来构建“类人智能体(human-like agent)”。我们尝试对人的知识、个性、记忆、道德、情感等方面建模,使得 AI 将来能够成为虚拟人,为人类提供情绪支持,成为数字员工(digital worker)、数字伴侣(digital companion),或真人复刻(replica)。除了技术之外,我们也做了一些能产生社会影响、呵护人间烟火的事情,比如用 AI 进行阿尔兹海默症的筛查,以及尝试用 AI 来给儿童提供情感陪伴。
4
人工智能领域的共识和分歧
AI 领域发展非常快,有些方面已经达成共识,有些地方还存在分歧。一些共识比较确定,比如说“规模定律(scaling law)”,从预训练(pre-train)到后训练(post-train),到测试时(test-time),包括上下文(context)越来越长,最后转成记忆(memory),这都体现了规模定律。另一个确定的就是计算和推理成本会显著降低,可能每年降低十倍,这样就使得更多的场景能以更低的成本使用 AI。共识还有强化学习及其支持性框架也会越来越强大。另外,多模态如果能够把视觉、语音、图像这些不同类型信息统一成词元化(unified tokenization)的表达,那么整个现有的框架就可以进行复用。其他共识还包括 AI 智能体的各种应用,如写代码、做研究等等,还有在线学习方面的应用。
还有一个是关于开源。我们越来越觉得未来开源模型在能力上和闭源模型会越来越接近,有可能开源和闭源模型在大模型应用的比例可能是 80:20,也就是说,全世界 80% 的应用或者模型会构建在开源基础上,开源和闭源模型可能会存在一些能力上的差异,但这个差距会越来越小。
值得一提的是尚未达成共识的部分,因为随着技术快速发展、领域快速迭代,现在我们觉得对的方式将来可能发现不对。比如,有人说预训练是不是已经走到了尽头,再继续训练下去的话对模型提升不会有更大帮助。一个典型的例子是 OpenAI 的 GPT-5 迟迟没有发布,大家怀疑这是因为计算资源的限制,还是有了计算资源但没有取得更好效果,还是说大规模训练本身需要不同的路径选择。这些问题目前都还没有清楚的答案。
另一个问题是多模态(multimodality)是不是真的能够提升智能水平?我们看到自然语言文本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但加入图像、语音数据后,并没有发现智能上有显著提升。多模态训练或学习是否真的能够提升智能,这还存在疑问。
现在大家都知道智能体工作流(agent workflow)很重要,通过不同的智能体来构建一个工作流,能解决很多复杂的实际问题,比如最近中国的创业公司 Manus 就搭建了这样一个平台。但真正的问题是,智能体工作流是像 Manus 那样基于人对于已有流程的理解来构建的,还是未来会完全基于 AI 来自动构建一套新的工作流,通过与环境的交互,对于反馈信号的学习,构建出甚至比人现有的工作流更好的流程?这也是一个有待探索的方向。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模型评估。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模型评估都是基于通用标准(general benchmark),比如数学题、多语言翻译、考试题等等,最近大家正好在关心大语言模型回答高考题目的结果如何。但从实际应用的角度讲,我们更需要评估的是在特定应用场景中、针对特定任务,这些模型到底表现如何。因此,基于给定领域和给定任务的模型评估,可能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还有一个问题是模型(model)和产品(product)之间的关系。有一种说法认为模型就是产品,随着模型越来越强大,产品可能就不再需要设计了,只要调用模型的 API 就能满足用户需求了。但在模型能力还不具备的时候,是不是产品还有一些价值,是不是模型能力加上产品价值能更好满足人的需求?这也值得探索。
其他存在分歧的问题还包括 AI 在将来会多个模型并存,还是单个模型一统天下?以及最终的通用人工智能(AGI)会是什么样子?我个人其实很少讲 AGI,因为 AGI 这个词很宏大,但是在实践中大家对 AGI 有不同的理解。有的人认为 AGI 是在所有任务上超越人类,后来发现这个定义过于宏大,就改成了“在 90% 的任务上超过 90% 的人类”,再慢慢变成“在某些任务上超过专家”。所以 AGI 这个词还没有被很好的定义。但我们期待以大语言模型、基础模型为代表的这套 AI 技术,能够在很多任务场景中给人类现有的工作带来效率提升,带来更大的价值。
5
人工智能发展的未来
回到 AI 发展的周期性视角。在早期的 AI 发展中,知识和数据是分离的(knowledge and data);而现在,知识越来越多地内嵌于数据中(knowledge embedded in data)。未来趋势是什么?是说人类以前的知识都不需要了,完全用数据让模型去学习就够了?还是说我们需要找到有效方式把人类已有的知识灌入到模型训练中,从而减少训练成本,提高模型的可干预性、可解释性等等?这是一种思路。
另一种思路来自康奈尔大学的教授 Richard Sutton,他写过一篇文章“The Bitter Lesson”,结论是过去我们在 AI 开发上的痛苦教训在于,人类为特定任务设计的各种专业知识,最终都被计算能力的提升所替代。他认为,我们不需要加入人类知识,一切都应从数据中学习,只要模型足够大、数据足够多,规模定律能够解决所有问题。这目前也不是一个共识。但随着大模型的发展,大约 90% 的人开始相信这个观点,还有 10% 的人仍在思考是否存在其他可能的路径。
相关文章

IT之家 7 月 12 日消息,科技媒体 Gsmarena 昨日(7 月 11 日)发布博文,分享了关于三星 Galaxy S25 FE 手机的信息,...
2025-07-12 0

7月11日,南京阿里中心在河西中央科创区正式开园。作为该区域规模最大的互联网园区,项目总投资超80亿元,总建筑面积达85万平方米。园区内规划建设了6栋...
2025-07-12 1

全球家电业正在进入新一轮的调整期:江森自控出售家用和轻型商用暖通空调业务,博世80亿美元接盘;松下宣布裁员1万人,并对“松下电器株式会社”进行重组;三...
2025-07-12 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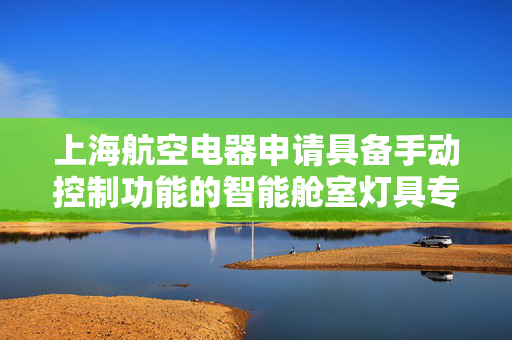
金融界2025年7月11日消息,国家知识产权局信息显示,上海航空电器有限公司申请一项名为“一种具备手动控制功能的智能舱室灯具”的专利,公开号CN120...
2025-07-12 0

防走失,电梯直达安全岛报人刘亚东A 来源:APPSO作者:发现明日产品的过去两周,AI 行业最出圈的不是哪个产品,而是人。经常一觉醒来,社交媒体的时间...
2025-07-12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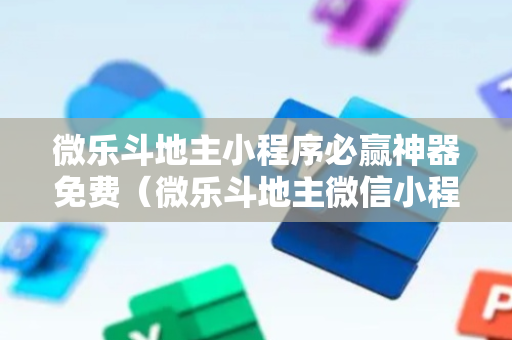
今天给各位分享微乐斗地主小程序必赢神器免费的知识,其中也会对微乐斗地主微信小程序免费挂下载进行解释,如果能碰巧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别忘了关注本站,现...
2025-07-12 1

这几年,谁能想到,来自中国的冥币,会在海外红得发紫。你没看错,冥币,这种中国传统祭祀用的纸钱,在国外火了。火到什么程度?法国街头万圣节一摆摊,冥币成了...
2025-07-12 0

今天给各位分享微乐斗地主透视软件免费下载的知识,其中也会对透视看牌器app进行解释,如果能碰巧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别忘了关注本站,现在开始吧!微乐斗...
2025-07-12 0
发表评论